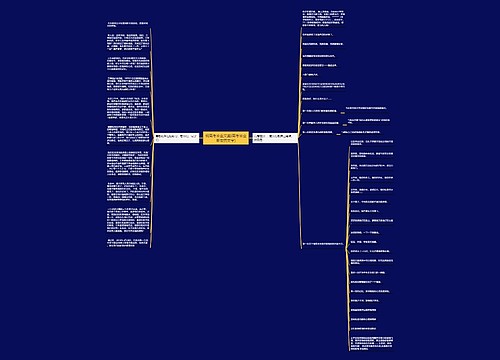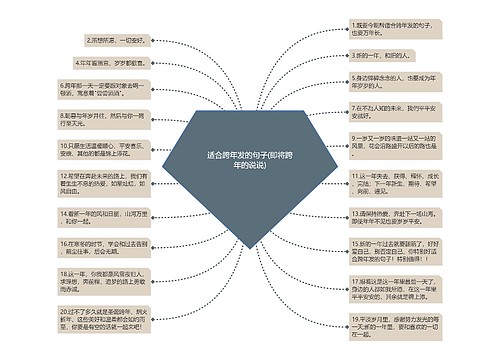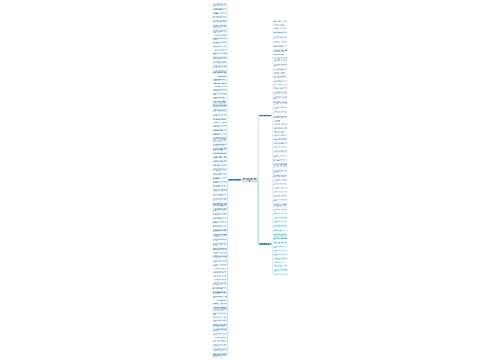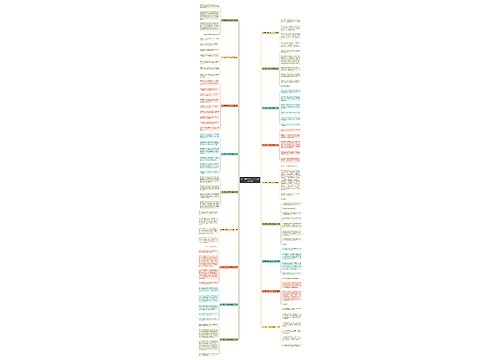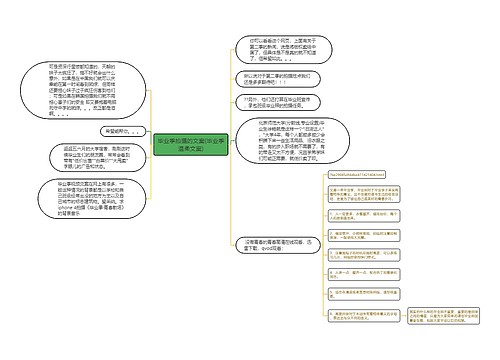不知不觉不喜欢过年的句子,冬天已来到我们身边。冬天在四季里有种自己特有的风情,它沉静、素简、内敛,却也浪漫、诗意、温馨。皑皑的白雪,温暖的炉火,热腾腾的火锅……这些冬天的美事,可以有了!
冬日,户外寒风呼啸梨花飞舞,屋内却炉火冉冉暖意融融,三五好友围坐在一起,泡壶热茶或小酌一杯,身心都热热乎乎的,空气里氤氲的全是温柔与沉醉。灯火之下,大家脸色泛红,漫不经心地吃喝、闲聊,不时碰杯、发出大笑,幸福的感觉就这样一点点漾开。
"我留了一盏灯,在满城风雪之夜,只要你,带着酒来,不说万水千山,不说相见恨晚。"
冬天和被窝是绝配吧,好像只要躺在软软的床上,人就会被"封印",失去抵抗的能力,满足中带着满满的安全感,梦也被暖烘烘地托起。"冬天应该睡懒觉,做长梦,在梦里见到想见的人。"
放了寒假,就可以睡懒觉。棉衣在炉子上烘过了,起来就不是很困难了。尤其是,棉鞋烘得热热的,穿进去真是舒服。(汪曾祺《冬天》)
一到冬天,猫便会从家里各处"长"出来:暖气片上,被窝里,衣柜深处……当然,还有你的怀里。为了寻求温暖,它们会卸掉一些高冷,与你贴近,你摸着它们柔软的毛发,会觉得心里软乎乎的,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治愈和幸福。
我同虎子和咪咪都有深厚的感情。每天晚上,它们俩抢着到我床上去睡觉。在冬天,我在棉被上面特别铺上了一块布,供它们躺卧。我有时候半夜里醒来,神志一清醒,觉得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压在我身上,一股暖气仿佛透过了两层棉被,扑到我的双腿上。(季羡林《老猫》)
"冬天就应该被温暖的东西围绕,有很多好吃的食物,灶台旁摞着干净的碗碟,胖胖的土锅里炖着肉、闷着饭、蒸着白白的馒头,房间里有灶火,烧着水,冒着热烘烘的蒸汽……"天冷了,吃点什么好呢?
冬天来到的时候,王琦瑶便在自己家烧一个火锅,一个坐一边,边吃边说话,时间不知不觉地溜走,天色渐暗,那火锅却越烧越暖。(王安忆《长恨歌》)
屋外暴风雪,卧房,炉火糖粥。暴风雪,糖粥,因为一个我。所有的幸福,全是这样得来的。(木心)
在寒风凛冽的时候,就围在暖洋洋的炉火旁,烤着红薯忆往昔。人在冬天,总是没有距离。(汪国真《人在冬天》)
冬天,生一个铜火盆,丢几个栗子在通红的炭火里,一会儿,砰的一声,蹦出一个裂了壳的熟栗子,抓起来,在手里来回倒,连连吹气,剥壳入口,香甜无比,是雪天的乐事。(汪曾祺《栗子》)
冬天卖"糖葫芦",蘸冰糖的才好吃。各种原料皆可制糖葫芦,唯以"山里红"为正宗。(梁实秋《北平的零食小贩》)
有一些剧和电影,似乎是专属冬天的。《步步惊心》和《琅琊榜》里的雪,这么多年仍让人念念不忘不喜欢过年的句子;《请回答1988》和《情书》,是多少人的"冬日必看"……那些温暖美好的感情,那些故事里的温度,那些追剧时的意难平,在每个冬天一一复燃。
外面下着雨,天色阴阴的,在不开灯的房间里一边听着雨声一边看剧,就是冬天最幸福的时刻。(@cici弦)
古时候,晒太阳有个雅称,叫"负暄","冬日负暄",是被许多人钟爱的美事。可不是吗,冬天的阳光一点也不晒,打在身上只有些微微的暖,惬意极了,若是有一把舒服的摇椅,再搭块毯子,简直随时可以滑进一个阳光味的梦。
太阳好的时候,只要不刮风,那真和暖得不像冬天。一家人都坐在庭间曝日,甚至于吃午饭也在屋外,像夏天的晚饭一样。日光晒到哪里,就把椅凳移到哪里。(夏丏尊《白马湖之冬》)
我在躲避冬天之前,先到瓦尔登的东北岸去,在那里,太阳从刚松和石岸上映照过来,成了湖上的一座火炉;此时,我趁机晒晒太阳,暖和暖和,这样做比生火取暖更让我感到愉快。(〔美〕梭罗《瓦尔登湖》)
没有雪的冬天,好像总有点遗憾,看天地白头,是一种浪漫,所以,等一场雪落好像成了对冬天的一种期盼。有一种欣喜,是在某个冬日的清晨,拉开窗帘,忽地撞见满眼素色。
对喜欢书的人来说,任何一个季节都是读书的良辰。若一定要说冬日读书的优势,大约在于它的素简,干扰较少,心较沉静,于是收获也更出其不意。冬日寂冷,而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温度。
读书时,须放开心胸,仰视浮云。或在暮春之夕,与你们的爱人,携手同行,共到野外读《离骚》经;或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林语堂《读书的艺术》)
冬天好像特别适合回忆,尤其是那些幸福的回忆,也许是因为天气太冷,格外能叫人想起那些生命中的爱、暖和美好。
记得小时候住在山东烟台,每年冬天都下着"深可没膝"的大雪。扫到路边的雪足有半人多高,我和堂兄表兄们打雪仗,堆雪人。那雪人的眼睛是用煤球"镶"的,雪人的嘴是捅进了一颗小"福桔",十分生动夺目。我多么想念我童年时代的大雪呵!(冰心《我喜欢下雪的天》)
在冬天,和家人在一起,共享一盏朦胧而温暖的灯火,共食一桌家常但暖胃的饭菜,就是最大的幸福。灯光,炉火,热茶,饭菜,亲情——有了这些,就有生活的趣味,就不再惧怕漫天的冰雪与世间的严寒。
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是"小洋锅"(铝锅)白水煮豆腐,热腾腾的。
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儿三个。"洋炉子"太高了,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
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
无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朱自清《冬天》)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