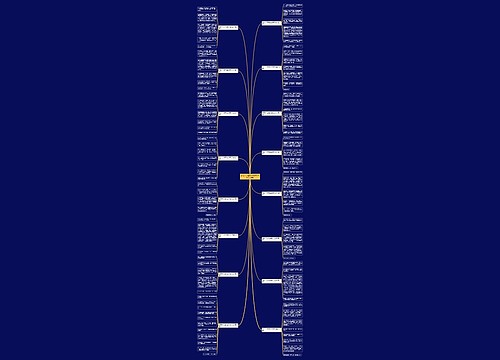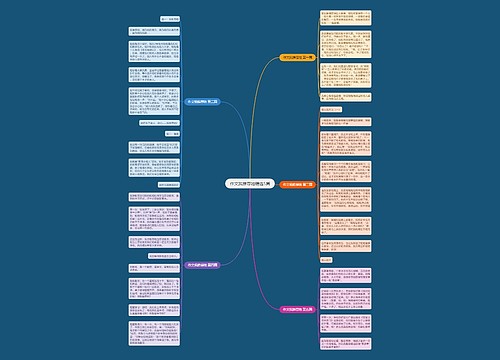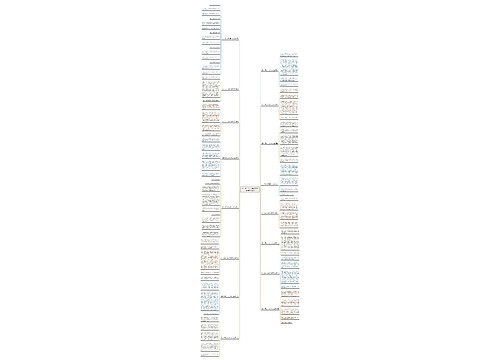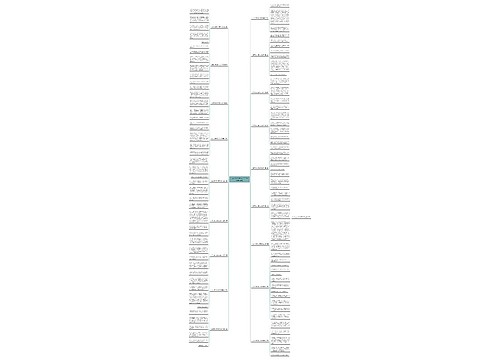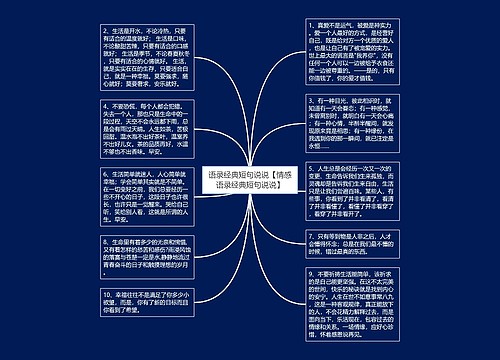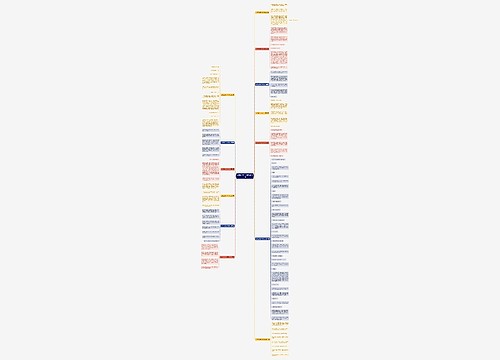文静的同学作文结尾共9篇思维导图
旧街悲巷
2023-05-09

文静的同学作文结尾 第一篇开头引用几句名言,或者比较精辟的话了,如:●青春是用意志的血滴和拼搏的汗水酿成的琼浆——历久弥香;青春是用不凋的希望和不灭的向往编织的彩虹——绚丽辉煌;青春是用永恒的执著和顽强的韧劲筑起的一道铜墙铁壁——固若金汤。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文静的同学作文结尾共9篇》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文静的同学作文结尾共9篇》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90d25c8461a0dc294cebb22d0cb4d27c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思维导图
 U633687664
U633687664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10b9a8a2dd2fb4593f8130ef16c320fc

9.战斗的基督教思维导图
 U582679646
U582679646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战斗的基督教》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战斗的基督教》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33d168acd0cd9f767f809c7a5df86e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