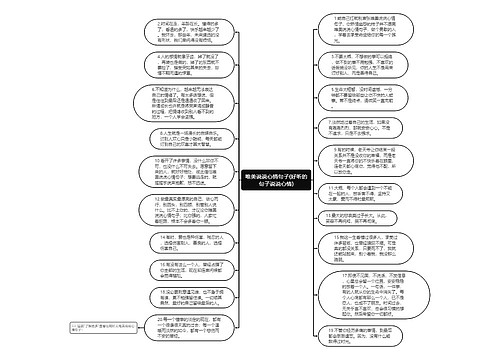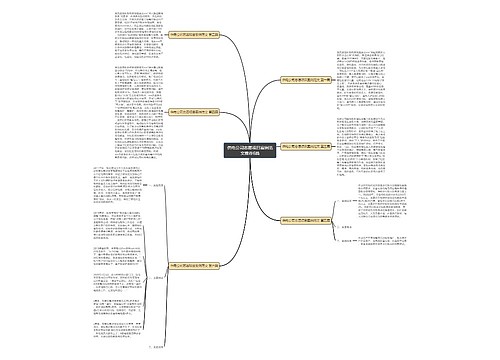六 莲花山轶事 三没牙老汉今年是吃不上自家的葡萄了。前些日子的特暖气候让他把那株冬藤过早地搭上了架子人们在春天,结果,那株他精心侍弄多年的葡萄藤在那场春雪中被冻死了。于是,这个村子里年龄最大、"见识最广"的人物发出了神汉般可怖的预言——这十年九不遇的怪天气预示着村子里要出事了。
没有谁理会他,也没有谁相信他的话,人们在春季里忙春播,在下种后那段短暂的农闲日子里到铁匠家看媒婆说亲。
这就是我们的莲花村,哪怕村东头有人放个屁,村西头立马就有人竖着耳朵听个仔细,张着嘴巴论个明白。
三没牙老汉戴上那顶几辈子没洗过的破帽子,干瘪着那张没牙的嘴,涎着口水,一边往铁匠家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人们在春天:"谁家的大姑娘生怪胎了,瞧这鬼天气,大天白日连个日头影儿也看不见。这铁匠也真是的,咋选了这么个灰日子请媒婆上门,真是一辈子也不会给娃娃们有个好兆头人们在春天!"他跟村里所有去铁匠家看媒婆的人一样,不过是想讨几颗烟抽抽,要是能碰上什么能嚼舌头的事,也好在村当街发表一下自个儿的"独特见解",至少不至于被"时代"淘汰。
这是一个多年少有的沙尘暴天气。漫天的黄土遮天蔽日,往日明媚的阳光也失去了动人的光彩,无论你身处何处,满鼻子都是呛人的土腥味,给人一种干呕的感觉。
铁匠的小家已经挤满了凑热闹的人。男人们嘴里叼着铁匠殷情递来的纸烟,女人们嗑着女主人端出来的瓜子。他们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吐着瓜子皮,又拿出一副关心仙花婚姻大事的神态,聆听着媒婆的介绍,玩味着媒婆的牙音,旁敲侧击地夸一夸仙花的美丽与他二哥的能干。这正是铁匠俩口所希望的,他们不仅要从媒婆的口中打听到对方的信息,也要将自己的情况告知媒婆。而我们的主人公又深谙"父不夸子"的古训,这些外来的口舌自然也就重要得多了。
外面恶劣的天气与室内融洽的气氛形成显明的对比。谈话很顺利:对方也是男大女小,又不傻不呆,只是因为家境有点困,不得已才换亲人们在春天;当家人也都老实正气,不是麻缠的主儿,这样的亲家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对娃们来说也是难得的福份……媒婆巧舌如簧,说得铁匠在一旁只有点头没有回口的份儿。
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仙花的情绪变化。老爹向她摊牌的一刹那,她的心忽而痛苦地紧缩了一下。她不是不爱二哥,更不想让二哥干光棍一个人生活下去,可她却没想到二哥的幸福竟是拿她的幸福来交换的。她爹的话不是没道理,可她还是在冥冥之中觉得哪儿有点不合适。这让我们的仙花感到为难,她实在没法跟爹妈提及自己与二后生的事。她没上过学,书本上的东西知之甚少,她不会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话。传统的意识里,她觉得一个人的婚姻大事好像必须由父母做主才算完美,其它一切好像都是什么歪门邪道。潜意识里,她又分明感觉到,自己的事总归自己管吧。比如自己和二后生的事,凭什么要别人掺和才算数呢人们在春天?可话又说回来,真这样做下去,二哥又该怎么办呢?难道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打光棍?仙花的心碎了,一夜之间,她的少女时代仿佛已经结束了。她的天真、纯洁、幼稚,瞬间灰飞烟灭,消失殆尽。她那憔悴的眼睛顿时变得那样的黯淡无光,和以前的仙花简直判若两人。
她没有少女那种因为媒婆上门而含羞带悦的表情,而是躲在最暗的角落里偷偷地抹眼泪。昏暗的天气帮她掩饰着这一切,她表面上尽可能多地以各种方式做出无所谓的样子,而内心却狂风巨澜般翻腾着: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她实在没有意识到人生的所谓婚嫁聘娶于她来得这么突然,这么仓促,以至于她就像过河时不慎掉进了深水之中一样,几乎来不及透一口气,河水就呛进了她的鼻腔,钻进了她的肺腑。她恍惚间也看见了岸上的行人,却连呼一声"救命"的时间都没有就沉了下去。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少女的羞涩让她无所适从。她没有任何可以倾诉的地方,也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父母已经像换牲口一样将自己出卖了,二哥又巴不得对方的女子早点过来做他的新娘。这种境地实在让我们的仙花难堪。找二后生商量吗?他又算什么人呢?何况,他又能帮什么忙呢?再说,他又是全村人通认的"铜货",万一出了面犟起老爹的驴脾气,说不定还会捅出什么大漏子,真要那样的话,自己这张脸又往哪儿搁呢?
院子里传来年轻人轻浮的笑声。这是山娃他们在看热闹,没准又在开谁的什么难堪玩笑,因为笑声里隐藏着一股很肉麻的情调。
二后生不会在其中的,因为这是给他心爱的姑娘做媒,他的心情一定是苦涩的,怎能也随着那帮愣小子瞎掺和呢?
天空渐渐地红了起来,那是一种骇人的凄惨的红色,仿佛天神因战斗流血而染红了苍天一般。风忽而紧得要命,随之而来的是劈啪作响的古怪的雨点。之所以古怪,是因为这与其说是雨点,倒不如说是正宗的泥点。
三没牙从低矮的中堂出来,揉着昏花的眼睛四下里瞅了瞅,枯着腮帮吐出一股烟雾,嘟哝着说:"娃们都是好娃娃,天气可是地道的败兴天气。"

 U182637395
U18263739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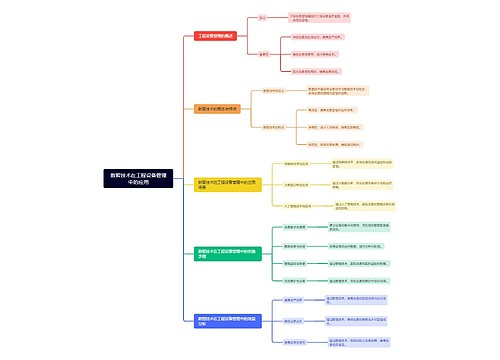
 U381614141
U381614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