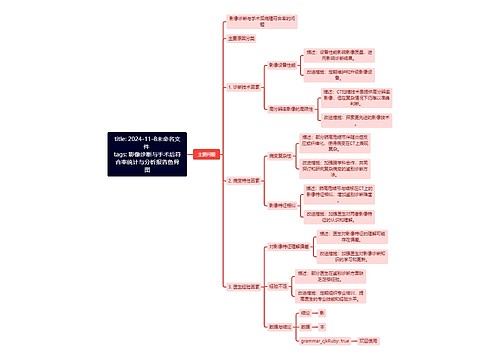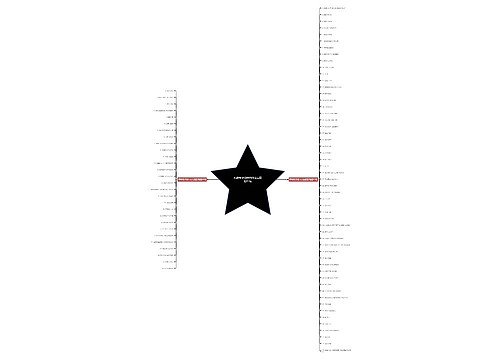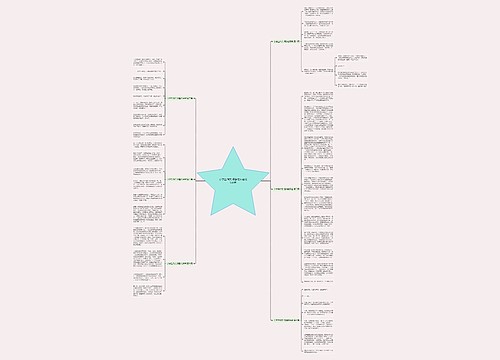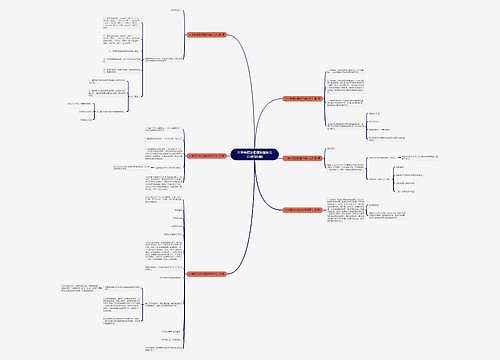那天飘着雪花。我这个宅老头因为有事要去医院,走出了家门。万万没有想到,竟在路上遇到了你。
你的头上,带着一顶似乎是粉红色的,用绒线编织而成的帽子 ;大大的口罩,将整个脸儿捂得严严的。我真的看不出是你。
或许看出了我的惊讶,你慢慢地将口罩的一边摘下;露出了半张脸。喔,是你!我即刻感到惊喜,继而感到惶恐。有什么想说吗?我真的有千言万语。能够兑现吗?我又委实不能保证。于是我显出了尴尬,支吾着。你是何等的聪明,抢先与我开口;只寒暄了几句,便微笑着向我告别。
我们相识多少年了?四十年有余吧?那时,你是天使;而我,则在地底下刨煤。相差如此悬殊,我哪里敢主动接触你!
真正与你接触,是我的一次意外事故。那次真的好险:一块三角铁板 ,从我的左上颌穿下,打掉了三颗牙齿;面部缝了几针,我早已忘记。可我清楚地记得,每隔两天,我就要到你那儿换一次药。你是那样的娴熟,那样的轻柔;你的手碰到我的脸,我的心便在抖。是紧张?是悸动?还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似乎感觉到了,于是和我闲聊。
我终于敢直面于你了,而且愈来愈放肆;竟至于敢和你争论。
记得那天患者极少,你为我换完药,便与我闲聊 。我们聊到了唐诗,说起了杜甫"三吏"中的《石壕吏》。当我背诵到"老妇出门看"时,你笑着打断了我,说:"错了,错了;不是老妇出门看,是老妇出看门。"现在我们早已知道,"出门看"与"出看门"两者都对,只是书的版本不同而已。可那时,我们却为此争的面红耳赤。
我面部的伤痊愈了,无需再到医院。可我俩,已经成为了真正的朋友。我不知你当时的感受;反正我一天不见你,便觉得寂寞的很,心里空落落的。幸好我家离医院很近,咱俩又是邻居,见面很容易。
我极想脱离井下那恶劣的工作环境,却毫无办法可想。你说我不要志气:"你不能多学点知识,靠你自己的知识离开井下?"你的表情是那样的严肃,"人活着,靠谁也不如靠己!"
说实话,多学点知识并靠它离开井下,是我常常萌生的想法。可惜也只是想法而已,从没有去实践。既然你也要我那样,那我就去做,决不让你失望!你坚定了我的信心。于是我远离了象棋、扑克与一切扯皮,开始了我除却上班便努力自学的生活。
可是,让只有初中功底的我,去啃那晦涩难懂的古汉语,真是难呀!我萌生了退缩的念头。
"无志之人常立志,有志之人立志长。"你满脸的失望,甚至带着愤怒,"我就知道,你根本就不是那有志之人!"
我带着无比的羞愧,离开了你。但我重新拿起了,那晦涩难懂的古汉语。
医院搬走了,搬到了新址;离我家很远。你也搬走了,搬到了医院的旁边;你离我也很远。
你安慰我:"你可以到医院看我,正好我自己一个办公室,活也很少。"
此时,虽然我的人事关系仍在采区,但我已经离开了井下,在职工培训学校做老师;时间倒是有的,便总去看你。我经常到了午间也不走;你便到食堂打来饭菜,我俩就在你的办公室里,一边聊着一边吃。
现在想想,真觉得好笑与奇怪:年轻时,我俩怎么那么多的话?!好像总也说不完。
那天我又去看你。刚进走廊,便遇到了你们的院长。他紧紧靠着我,拍着我的后背小声问:"又来看她?"真不知为什么,我瞬间竟窘得不行,支吾起来。院长倒是很亲切,仍旧小声说:"你这个才子呀,一眼就能让人家看出你的心。"他把我拉进了他的办公室,让我坐下;然后严肃起来。"你听到没?最近在我们医院,有关你俩的传言可不少。"我无语,脸红起来。"以后你最好少来看她;"院长说,"她是医院的重点培养对象。你给她造成影响,影响了她的前途;不好吧?"我赶忙起身解释:"不是看她。我头疼,来医院是为了开点止痛药。"院长哈哈大笑:"你这小子,还开啥止疼药?我这就有。"说着,他打开抽屉,拿出了一大联扑热息痛;递给了我。我连"谢谢"也忘记了说,夺门而出,逃离了医院。
或许,你融入了我的精神里,我已无法将你忘记。每有机会,我无需控制自己,依旧到矿山看你。让人们去说吧,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你我不必去理。
此刻,你从我的身边离去;让我躲开了惶惑与尴尬。天空依旧飘着雪花;我是否还有机会见到你?
我们都老了。你已经搬迁到了外地。我真应该追随你去那里。可惜,我们的差距依然太大;更何况我还有儿女!
请你接受我这个老朋友的祝福吧。由衷地祝福你快乐健康,事事如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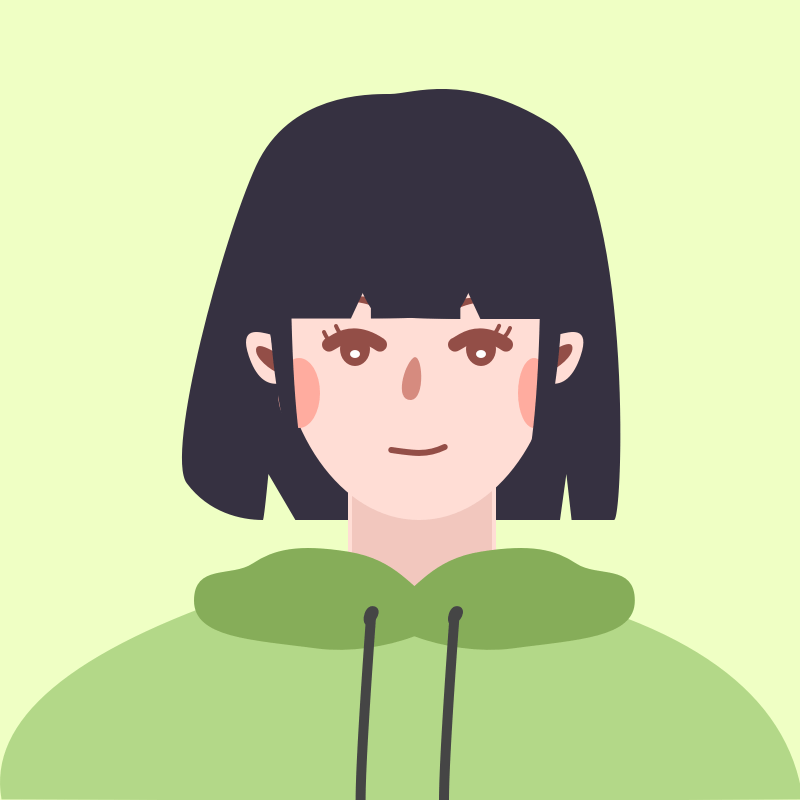 U979745175
U97974517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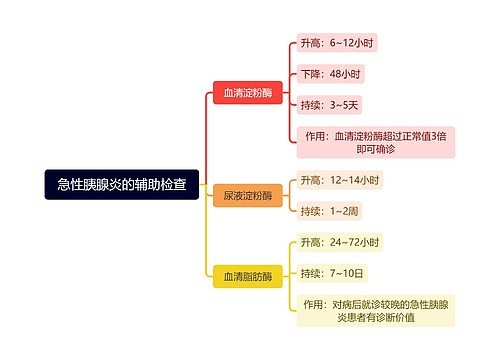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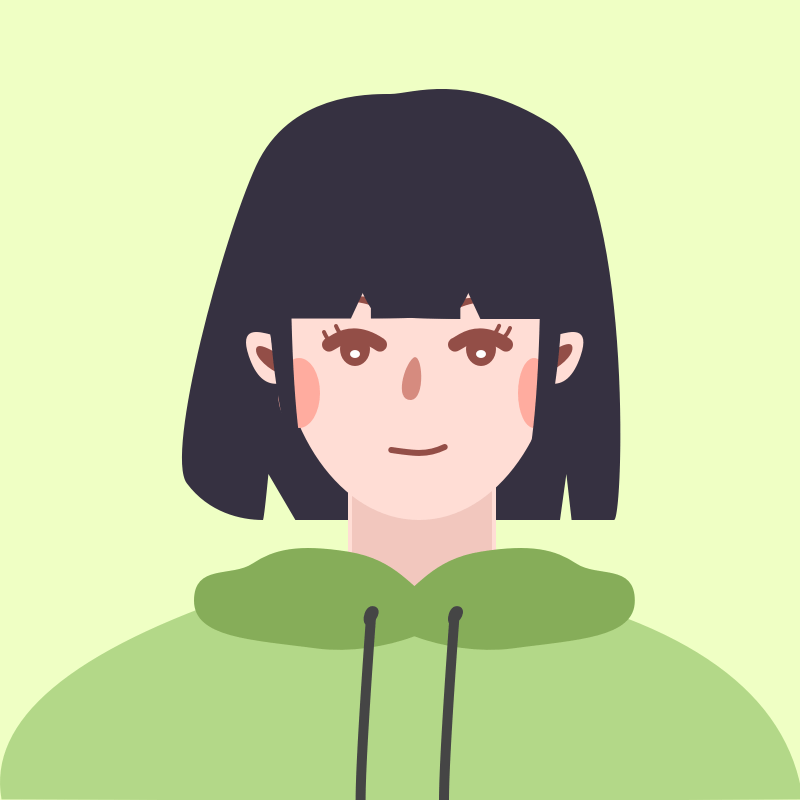 U880271396
U880271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