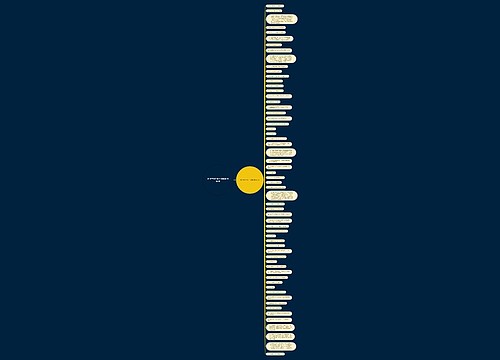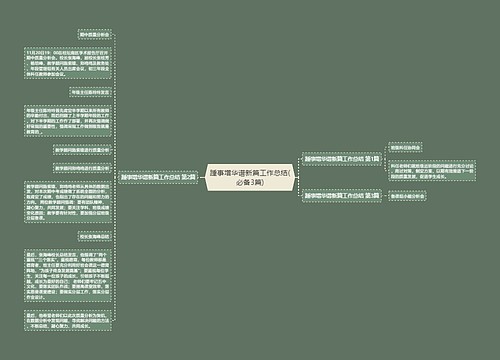自从他考上大学,就很少回过老家。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让他眩晕、痴迷、幸福、不知所措。他拼命学习,只为让这座陌生的城市能够接纳他。最终他真的留在城市了,并且通过贷款,购买了一套3室一厅的住宅。母亲没有来过城市。他连婚礼都是在城里举行的。
婚后好几年,除了春节,他从来不曾回过老家。儿子想奶奶,跟他闹了好几天,最后他只好跟妻子商量能不能把母亲接过来住些日子。妻子同意后,他给母亲打了个电话。他说您来住一些日子吧。母亲说我在城里住不习惯。他说您就来吧,小宝说他想奶奶。母亲想了想,最后说,好吧。
就这样母亲来到了城市。那是她第一次来到城市,城市让她极不舒服。
母亲带来两个蛇皮口袋。一个口袋里装满刚从菜园里摘下的新鲜蔬菜,一个口袋里装满刚从地里掰下的青玉米。那样的蔬菜城市里到处都有卖,价格很便宜;那样的青玉米卖得更多,他们早已经吃腻了。母亲带来她所能带过来的乡下的所有,却唯独没有带来乡下的习惯。她战战兢兢地在屋子里走动,小心翼翼地和他以及他的妻子说话。五十多岁的母亲知道城市和乡村的区别,知道装修豪华的楼房和简陋的乡下草屋的区别,即使住在儿子家,她也不能太随便。
他忙,不可能时时陪着母亲。妻子也忙,她得去公司上班,去健身房健身,去电影院看热播的大片,去业余班学英语、学会计……他们把母亲留在家里,让儿子陪着她。妻子对母亲说,这是马桶,按下小钮,冲半桶水,按下大钮,冲整桶水;给小宝热牛奶的时候,用燃气灶,往右拧这个开关,就能打着火……
母亲的表情就像一个懵懂的孩子。这么多事,这么多规矩,她怕记不过来。
母亲小心翼翼地关上门,愣愣地坐在沙发上。她不敢用抽水马桶,不敢动电视,不敢开冰箱,不敢接电话。后来她不得不硬着头皮打开了燃气灶,为自己的孙子煮了一杯牛奶。那个上午她只动了燃气灶,却差点儿闯下了天大的祸。
中午他回家时,闻到一股很浓的煤气味。孩子在卧室里睡觉,母亲坐在沙发上择着青菜。见了他,母亲说,我头有些晕。他不答话,冲进厨房,见燃气灶的开关开着,正咝咝地响。他连忙关掉燃气灶,打开厨房的窗户,又冲进卧室,打开阳台的窗户。他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跑,一扇窗子一扇窗子打开,母亲惊恐地看着他,脸色苍白。母亲说出什么事了吗?他说没事,脸却黑得可怕。母亲垂下头,她知道自己肯定闯下了祸。她不敢多说一句话。
妻子还是知道了这件事。晚上她把母亲叫到厨房,再一次跟她讲解燃气灶的用法。她说多险啊,如果不是他中午回了趟家……母亲说我吹不灭火,就用湿毛巾把火捂灭了。母亲说我不住了,在城里真住不习惯,以后,还不知道会闯下什么祸……
母亲第二天就回了乡下。这时他才想起来,母亲竟一次也没有用过家里的洗手间。母亲腿脚不便,可是她仍然坚持去一公里以外的公厕。母亲留下的那些青菜和青玉米,他们吃了很长时间,还是没能吃完。最后只好扔掉了。
第二年春天他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故。妻子带着儿子与他离了婚,一个完整的家瞬间破碎。那些日子他每天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终于被公司解聘了。他重新变得一无所有,整天闷在家里,借酒浇愁。终于有一天,他在横穿马路的时候,被一辆汽车撞倒在地。虽然没什么大碍,可是需要卧床养伤。医生说,你需要在床上至少躺半年的时间。
母亲再一次进了城。这次是母亲主动要求来的。他不想让母亲看到他现在的可怜模样,他劝她不要来了。母亲说我还是去住些日子吧!他说您不是住不习惯吗?母亲说会习惯的。来的当天母亲就用燃气灶给他煮了晚饭。母亲说,你放心,煮完饭,我不会忘记关掉燃气灶的。
他惊讶地发现,母亲竟然表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她把冰箱整理得井井有条,每次关冰箱,都不忘看看冰箱门是否关严;她修好了一把断了一条腿的木椅;她把空调的温度调得恰到好处;每当有敲门声,她总是先问一声谁啊,然后再通过猫眼看清门外的来人;她把洗手间和地板拖得一尘不染;她用微波炉给他烤面包;用果汁机给他榨新鲜的果汁。甚至,母亲还帮他发过一个传真,那是他的一份求职材料。
母亲在几天之内迅速变成了一位标准的城市老太太。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自己的儿子,就像在乡下照顾小时候的他。后来他的心情好了一些,没事的时候,就和母亲聊天。母亲说昨天我去超市买菜,问楼下的老大姐,她说现在写作得用电脑。他说都扔这么多年了,还是算了吧。母亲说不能算了,我明天给你去电脑城问问。我问过那位大姐,她说组装的电脑会便宜一些。我有钱呢。母亲说完,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纸包,打开,里面包了一沓钱。母亲说是我这几年攒的,四千多块钱,给你买台电脑吧。
第二天,母亲真的一个人去了电脑城。中午她没有回家,只是打回来一个电话。她说你要17的显示器还是19的显示器?17的便宜,也清晰,但太小,看着可能累眼睛。内存和显卡……那一刻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跟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识的字肯定不会超过100个的农村老人,竟然说出了显示器、内存、显卡!只要他需要,那么,母亲就必须弄明白这些。因为她在为他做事,因为她是他的母亲。
电脑买回来后,他真的开始了写作。开始当然不顺利,不过也零星发表了一些。随着发表量越来越大,他的心情也越来越好。半年以后,他几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想,假如没有母亲的鼓励,假如没有这台电脑,那么,他不知道自己那种灰暗的心情,还能够持续多久,他会不会天天泡在酒杯里,永远消沉下去。现在他彻底忘掉了自己的不幸,感觉生活一天比一天美好。
突然有一天,母亲在客厅里摔了一跤。他过去扶起母亲,母亲说,地板太滑了,这城里,我怎么也住不习惯。那一刻他努力抑制了自己的眼泪——母亲为了他,几乎适应了城市的一切;而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让这个家适应自己的母亲,哪怕是换成防滑的木地板。
他说明天我就找人把地板换成地毯。母亲说不用了,明天我想回去。他问为什么?母亲说因为你已经不再需要我的照顾,我留在这里,只会耽误你写作。还有,地里的庄稼也该收了,怕你爹他一个人忙不过来。
他求母亲再住些日子,可是母亲说什么也不肯。她说我真的住不习惯。地板、燃气灶、微波炉、冰箱……都不习惯。如果你想我了,就回乡下看我。
他叫一声妈,泪水滂沱——当母亲认为他需要自己,她会迅速改变自己多年的习惯,变成一位标准的城市老太太;而当她认为自己已成为累赘,又会迅速恢复自己的习惯,重新变回一位年老的农妇,远离儿子而去。似乎她的一切都是为他而存在,为他而改变。她的心里面,唯独没有她自己。
母亲,在您的身边,我永远也长不大。您,离开我十几年了,记忆,像肥皂泡,一个一个,随风飘落。唯有您,悉悉索索的脚步声,夜里寻食的老鼠的脚步声,小心翼翼的脚步声,常常侵入我的梦林。轻轻地,轻轻地,一朵白云飘远,天国拥挤吗?昨夜,你有走进我的梦里。好温馨,好温馨,我又找到了家。
早晨,您从熟悉的灯台上,划一根火柴,蹑手蹑脚的,搁在锅台上,点亮了一天的生活。抱柴,给锅里添水,捅开灶膛的死灰。一袋烟工夫,香喷喷的早饭便做好了。我敢说:母亲做饭是一把高手,虽然她不识一个字,没看过一页关于烹调的书。她总能将有限的食材,调理的有滋有味。接下来,在全家端起碗,喂饱扁瘪的肠胃的时候,喂猪,拾掇家具上落下的灰尘,就连空的瓶瓶罐罐,都擦得铮亮,仿佛能照出人影。
接下来,就是上地干活。母亲的气力是很大的,干活从来不遛弯。那时候,生产队挣工分分红,母亲挣十分相当于一个男子劳力。母亲不仅力气大,而且干活很细心,她能把一棵玉米根底的草,剔除得干干净净。拉车,驾辕,点籽,扬粪,扶犁,样样是一把好手。干活的间隙,母亲常常揣着针线活,纳鞋底,绣鞋垫,纳的鞋底平整,鞋垫上的龙凤,展翅欲飞。
中午,母亲还是一溜烟的小跑,像捻线砣。做饭,洗碗,喂猪,洗衣服,打理院子里的瓜菜。记忆中,母亲是从不睡午觉的。好像她有使不完的劲。
晚上,特别是在夏天,夜很短。蚂蚱和蟋蟀在院子的菜地里,悠闲地弹琴,母亲就着橘黄的灯盏,做着针线活,背影在土墙上一起一伏。静谧的夜,总是编织着温暖,尽管外面的夜黑黑,尽管当时的日子大多的人家过得都很拮据。
儿行千里母担忧。如今,村子里和您一样年长的都去了,和您走一条道。村子里的窑洞,向张开口的喇叭,一片衰落。大多数人家的院子里,长满了蒿草,不敢跟您提及,您听了一定会惋惜的睡不着觉。村子里的人家,气力好的,都到外面讨生活去了,老弱病残的也不多了。只有村口老槐树上的麻雀,是最后一批留守者,灰灰的眼睛,见证着村子的荒凉。也许,它们生来就认为,那里是它们的永久的家园,根的所在。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