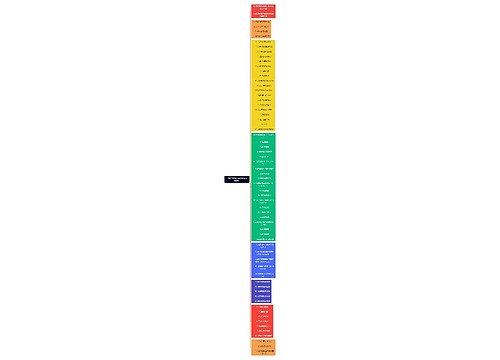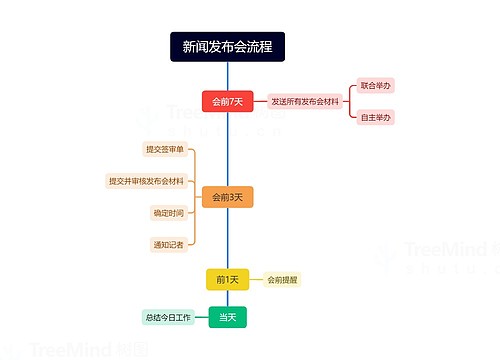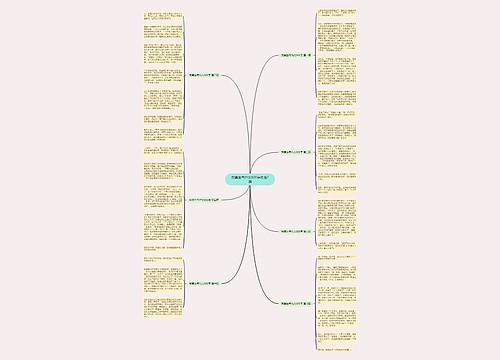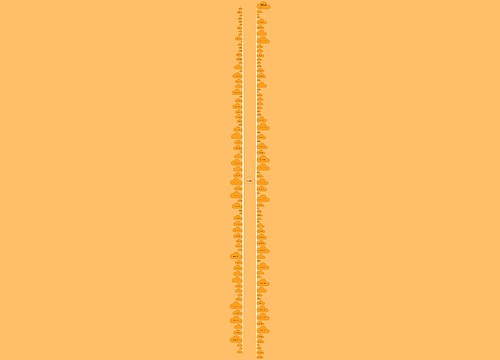读的是娘亲,我眼前晃出的却是父亲——罗中立的那幅油画。那张被苦难摧折得沟壑丛生的脸、黑得像酱油的汤、残破的碗,叠化在这文章的枝枝丫丫上,渐渐合二为一。
人都有这样的父母罢: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一辈子步履未出过巴掌大的村庄,默默劳作,默默受苦,默默老去。阿城的《棋王》里,棋呆子王一生的母亲平凡到一辈子没攒下买一副棋的钱,到处捡牙刷把,磨成棋子;不识字,就不刻,临终留给他。小说中用旁观者口吻写:"我鼻子有些酸,就低了眼,叹道:‘唉,当母亲的。’王一生不再说话,只是抽烟。"
对着这样的母亲,说"奉献",说"伟大",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总觉得浮,觉得作,觉得肉麻,觉得只会让她惊扰不安——也只能叹一声,说一句:唉,做母亲的。
这样的娘亲进城来了。她不知所措,她小心翼翼。那是一种认生,也是与时代脱钩带来的失重。中国一脚从农耕迈进信息时代,本来该几百年走完的路,一步就跨过来了。步子好跨,人心难搬。把你直接扔到几百年后,你也茫然。眼前看着有门,但是老了,既看不懂,也推不开。
幸好,还有一个站在门里的儿子。儿子不急。耐心陪伴、淡淡说明。文中最动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可以读出,在他的轻声抚慰下,娘亲的心情如同茶叶入水,慢慢舒展开。
娘亲的味觉停留在玉米糊糊中,喝拿铁,她觉得"糊锅"了,那有什么要紧?不去莽撞撞"纠正",不去急吼吼"启蒙",没有文化傲慢,只是带她去喝。或许下次,娘亲就能咂摸出点儿滋味来呢。唯有这种陪伴,才可以慢慢磨平由于跨越发展带来的代际沟壑。
中华文明不是最古老的文明,但却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文明。
一代一代人如同一节一节列车车厢,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前后相连,哪怕风雨大作的危险路段,几经摇晃,也挺了过来。如今车入大野,风驰电掣,车厢间的联结要更结实、更圆润才是——好穿过更加波澜壮阔也免不了风雷激荡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