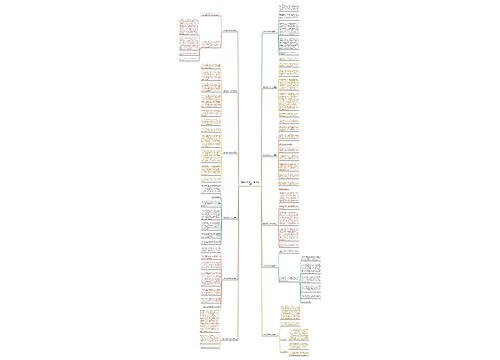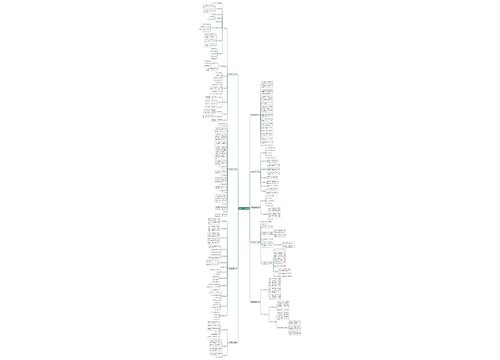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优选17篇思维导图
感情愚钝
2023-05-08

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优选17篇
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 第一篇妈妈喜欢吃荔枝,家里的桌子上最近总是有很多荔枝,但我不喜欢吃,我觉得它太酸了,酸得我无法忍受。我记得小时候我吃过几次荔枝,那时候还挺喜欢吃的,觉得咬上去虽然酸酸的,可是总有一丝丝甜味,颇有种“苦尽甘来”的感觉。酸甜两种滋味混合在一起,简直爽歪了。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优选17篇》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优选17篇》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bee7f8687dcc54f5759b47d7b4590bb6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优选17篇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 第一篇
妈妈喜欢吃荔枝,家里的桌子上最近总是有很多荔枝,但我不喜欢吃,我觉得它太酸了,酸得我无法忍受。
我记得小时候我吃过几次荔枝,那时候还挺喜欢吃的,觉得咬上去虽然酸酸的,可是总有一丝丝甜味,颇有种"苦尽甘来"的感觉。酸甜两种滋味混合在一起,简直爽歪了。那时候我很少吃零食,对于水果可是求之不得,因此很喜欢吃这个很少出现在桌子上的荔枝了,可是长大后为什么不喜欢了呢?
也许是越长大越胆小吧,我开始惧怕了这种酸味,连最后的甜也不想去品尝了。
长大后的我们长得高了,目光宽阔了,视线里收纳的事物也愈来愈多了。一束光洒在沙滩上,小时候我们看见的是波光粼粼的大海与金光闪闪的沙滩,而长大后我们看见的,却是每一颗沙砾背后的阴影,以及汹涌波涛下的深海。比起欣赏美景,我们似乎更在意涨潮时海浪将我们吞没。
小时候的我们总是嚷着要快快长大,长大后的我们却叹息着想回到过去,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接受现实,即使我们回不到那个单纯幼稚的学生年代了,但我们也要保持着一颗纯真的心,相信未来,相信明天,相信面朝大海,能看见春暖花开。
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 第二篇
我在老家的一天下午,我写完作业后,姑妈带我和两个哥哥一起去下坝买吃的,但是,刚买完荔枝
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就大吃特吃,姑妈叮嘱我们:"少吃点,给爷爷,奶奶留一些。"我们很不服气,所以一下子全吃完了,害姑妈闹了一顿笑话。
成熟的荔枝像一个红通通的气球,他的外皮上有一些小小的刺,不过扎人不疼。而它里面的果肉是白色的,晶莹剔透。吃起来酸溜溜,甜津津美味极了。里面有一个黑色的种子。我吃的时候先把外皮剥开,然后,把种子剥掉,然后就把荔枝里的果肉吃掉。
当我回到家里,一看,堂哥流鼻血了,我便问姑妈:"怎么回事!"姑妈说:"一颗荔枝一把火"于是,我明白了:如果荔枝吃多了,就会像堂哥一样流鼻血,于是,我吃荔枝的次数便越来越少了。
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 第三篇
说到荔枝大家并不陌生吧,我今天就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荔枝。
荔枝是著名的南方水果,属亚热带水果,它原产我国南部,在杨贵妃那个时候就有了。荔枝汁甜味美,深受我们的喜爱。
荔枝一生生长在树上,一般是六七个月成熟,长成后呈球形或卵形,熟时为红色,果皮有明显的突起的硬皮质疙疙瘩瘩的小瘤体,肉体呈半透明状,晶莹中带着一丝雪白,晶莹剔透,惹人喜爱。荔枝喜欢光,喜欢暖热湿润气候,怕霜冻,喜欢温暖。
荔枝以果形别致、颜色悦目、果肉状如凝脂,香甜滑爽、清甜浓香、色味具佳而著称,其营养价值更是在种水果中鹤立鸡群。
荔枝是古今著名的养颜珍品,荔枝历史悠久,在几千年前的唐朝时就有了,而且常常是作为宫廷贡品进献给朝廷的,一般的贫穷人家是吃不到的。唐朝时,杨贵妃十分喜欢吃荔枝,荔枝含有养颜护肤的作用,后来造成"安史之乱"的安禄山知道了杨贵妃十分喜欢吃荔枝,就跑去南方,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那一车珍贵无比的荔枝送到了京城,以此得到了皇上和杨贵妃的信任。
荔枝不但好吃,还能用气味杀死虫子。可是,荔枝虽然好吃、能杀虫,但是,吃多了荔枝反而会上火和生病。所以我劝大家最好少吃点,不要为了一时之念吃多了荔枝,换来的是生病。
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 第四篇
荔枝是莆田四大名果之一,如果你问我我最爱吃什么水果,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我最喜欢的水果是荔枝!"正因为我这么喜欢吃荔枝,所以今天我就来介绍介绍荔枝。
荔枝只在每一年最热的时候——大暑成熟,当你站在专门种植荔枝的果园后面,远远的眺望荔枝树时,会发现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荔枝树仿佛不是荔枝树了,而是一棵棵挂满红宝石的树,样子,美丽极了。而且听说荔枝还有一句著名古诗句呢!"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就说明了荔枝在古代都那么的受欢迎,连古代的四大美女——杨贵妃都这么爱吃。
如果你把荔枝拿在手里,拨开那鲜红色的"外皮",吮吸那白的像雪一样的果肉时,你会感觉到你仿佛不是在吃荔枝,而是在吃着最香最甜的蜂蜜。但是这样并不是荔枝最好的吃法,如果你把荔枝先浸泡在盐水里大约十分钟,然后再放进冰箱冰镇一会儿。这时你再拿出来品尝,轻轻咬一口,吃了之后你会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冰天雪地似的,又冰又甜,吃了一个肯定会再吃一个,再吃一个!再吃一个!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听了我的介绍,你是不是开始喜欢吃荔枝或更加喜欢吃荔枝了。如果喜欢,那就到我的家乡——莆田来好好品尝荔枝吧!
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 第五篇
我的故乡在洋桥,我爱故乡的荔枝。
细雨如丝,一棵棵荔枝树贪婪地吮吸着春天的甘露。它们伸展着四季常绿的枝条,一片片狭长的叶子在雨雾中欢笑着。
5月过后,荔枝树上挂满了荔枝。
荔枝圆圆的,和乒乓球一样大小,遍身生着小刺儿。荔枝外面是鲜红鲜红的,果实却是白白的,还有一颗纯黑的小核。
荔枝先是浅绿的,随后变成深红的,你轻轻掰开它,马上就会流出可口的果汁,甜甜的。
没有熟透的荔枝又酸又甜,吃下去感觉像在喝酸水一样,熟透了就甜津津的,叫人越吃越爱吃。我小时侯,有一次吃荔枝吃得太多,之后吃的食物都好像没有味道,更没有胃口,那阵甜甜的荔枝味在我口中不肯散去,喝了几杯热水才感觉舒服多了。
爸爸说过民间流传一只荔枝三把火之说,荔枝吃得太多会上火,所以不能吃太多荔枝,
我爱的我的故乡,更爱故乡的佳果——荔枝。
宾阳县芦圩完小四年级 葛莹莹
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 第六篇
"红布包白布,白不包猪油,猪油包石头。"你猜这是什么水果呢?对,这是岭南佳果——荔枝。
荔枝的外皮有的红,有的黄,有的半红半黄……它外表粗糙,全身布满细小状裂片,好像乌龟和身上的龟裂,它长得还有点像小草莓呢!千万别嫌它长得丑,不然里面的美味你可就享受不到了哟!
荔枝的外表虽然粗糙,但是果肉很好吃,轻轻拨开它的皮,就会发现它还藏有一层薄薄的膜,这时你别着急去咬那膜,它会让你苦到怀疑人生的。剥完膜后吃下它的果肉,顿时一股又甜又凉的味道沁入心脾,会让你忍不住吃了一个又一个。可是荔枝吃多了是会上火的,没关系,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只要把荔枝养大盐水浸泡半小时以上在吃就可以去火啦!
荔枝不容是小觑的,它不仅好吃,还非常有营养价值及药用价值。荔枝还有丰富的糖、磷、维生素C和少量的蛋白质,他还可以驱寒美颜呢,怪不得从古至今一直都深受人们的喜爱。
这么美味可口的荔枝,你确定不尝一尝吗?
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 第七篇
你们摘过荔枝吗?在今年烈日炎炎的暑假里,我有幸体验摘荔枝的乐趣。
七月盛夏,天热得连蝴蝶都只敢在树荫下飞,好像怕阳光灼伤了它们美丽的翅膀。七月盛夏,湛蓝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
虽然天气如此炎热,但是丝毫没有阻碍荔枝的美丽。
在果园里:许许多多的荔枝挂在梢头,一个个荔枝像一盏盏小灯笼,红彤彤一片。一踏进这"绿红相间"的果林,就有一股淡淡的荔香神奇地从四面八方飘然而至,这种荔香闻了之后使人神清气爽,沁人心脾。逐渐浓厚起来,由远而近,由淡转浓……
看到如此可口的荔枝,我忍不住摘了一个细细的端详着,轻轻的闻着,慢慢的咬着,不住发出啧啧的赞叹声。好像有一股甘泉,流进我们的心田。
开始摘荔枝了。刚刚走入果林,便有一大群飞虫朝我们袭来。害得我们手上奇痒无比!可是最惨的是我,因为我穿得是比较短的裤子,所以我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摘荔枝的时候,除了昆虫与我们作对,太阳公公也生气了。夏日里的太阳火辣辣的,直射在人们的头顶上,就像从天空中降了一盆大火。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脸上铺满了汗水,所有的人都精疲力尽、气喘吁吁。说时迟那时快,我突然摔了一跤。而当时我很累,而裤子下面一点和衣服袖子都弄得全是泥巴,于是我不想再摘了。这时,妈妈说:乖儿子,这点儿小事你都坚持不了了?你想一想,那农民伯伯他们那么辛苦都能坚持下去,难道你就不能坚持吗,要知道古人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听了妈妈的一些话语,我顿时明白了: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总是会经历一些坎坎坷坷,只要有决心,有付出,才会有回报!才会收获成功!
这真是一个让我难忘又有收获的快乐暑假啊!
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 第八篇
今天晚上,我吃了荔枝,它是一种在初夏吃的水果。
它的形状轮廓有点像心形,又有点像圆形。颜色是红色的和淡绿色的,越红的越熟,而且一般的话上面比下面更红。摸起来很粗糙,上面有一个个小小的凸起,是围绕着一个柄向外生长的,于是,长到后来就长成了一个"刺球"了。
开荔枝皮也很难,有时剥开了最硬的外皮,但是里面还有两层软皮,也有点难剥。一旦剥开了软皮,里面就是一颗半透明的果肉,吃上一口,又甜又嫩又多汁。最里面是一颗小小的核,有一粒花生那么大,小的只有松子大小。
因为荔枝的甜美,所以关于荔枝的传闻和诗文不少。传说,杨贵妃喜欢吃荔枝,唐玄宗用千里马从岭南运来荔枝进京,一路上尘土飞扬,大家还以为发生了紧急的战况,杜牧于是题了一首叫《过华清宫》的诗,其中有一句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从此有了"妃子笑"这个名字。好美丽的名字,又是这样的讽刺。一个国君为搏妃子开心,劳师动众,真是很过分了。而周幽王为了博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结果是把自己的国家给玩掉了。
宋朝的苏轼也写过荔枝的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甜美的荔枝为客居在当时蛮荒的岭南的苏轼带来了很多的安慰。
荔枝作文03-26
荔枝的作文05-22
《荔枝》01-24
荔枝01-24
荔枝01-15
摘荔枝作文03-30
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 第九篇
在水果当中,我喜欢吃晶光耀眼的梨、甜津津的大桃子和红灯笼似的柿子,但我最喜欢吃的还是那诱人的荔枝。
成熟的荔枝,大多是深红或紫红色的。远远望去,像一颗诱人的"珊瑚珠"。
我从枝杈上剪下一个细看,荔枝的果是球形或卵形的,皮很粗糙,上面有一个凹凸不平的小疙瘩。在荔枝的顶端,有一个明显的疙瘩,荔枝是连接枝杈的。剥开皮,就露出晶莹剔透的果肉,摸上去滑滑的,软软的`。隔着果肉,可以看到荔枝中间的核,好像一颗黑珍珠。那润泽的果肉真让人不忍心去吃,但荔枝又那么令人馋涎欲滴。
刚放入口中,一腹浓浓的香甜之味,涌入肺腑。吃完了一个,可荔枝的香味还久久地留在口中,甜甜的,像吃蜜一样。这种感觉让我情不自禁地摘下了一个又一个……
荔枝,你是那样诱人,真叫人抵挡不住你的诱惑啊!
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 第十篇
来到广州,有几个地方是必去的景点,例如——荔枝湾涌,荔枝湾涌这几年可以说是广州的一张亮丽的旅游名片,它——是广州闻名的西关美食出处。
说起荔枝湾美食可谓半天也说不完啊!有肠粉,炸鱼皮,马蹄爽,牛羊杂汤等,其中,艇仔粥我就尤其喜欢,艇仔粥是以鱼片、炸花生、鲜虾等近十种配料加在粥中而成。原为一些水上人家用小船在荔枝湾的河面经营,因此品集多种原料之长,多而不杂,爽脆软滑,鲜甜香美,适合众人口味。
说到艇仔粥,它还有一段历史,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呢?相传有一个船上人家的女孩叫金水,心地非常善良。一日她把父亲捕到的一条鲤鱼放回到江里。几年后,金水的父亲患了重病,她非常伤心,来到江边祈求仙人保佑。这时一位仙女从水中出来说:"我是几年前被你救的鲤鱼。你只要煮一些鱼虾粥再加些油脆之物卖给人家,便可换钱带你爹去看大夫,10日之内即可痊愈。"金水依法照做治好了父亲的病。从此这粥就被取名为"艇仔粥"。
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 第十一篇
在荔枝公园,沿着草坪上的小路走过去,是一大片荔枝园。
夏天,荔枝挂满了树枝,火红的荔枝星星点点,十分好看,还散发着一阵迷人的果香,这里的空气像荔枝一样香甜。
这就是虫虫们的故乡荔枝村,多么美丽的村庄呀,真是虫虫们的天堂。
这里有荔枝核做的房子,像球一样严包密裹,小蚂蚁打开天窗,就能看见满天的星星,那是空中飞舞的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树上还有许多的洞洞,有的深,有的浅,每一个都是一个安全阴凉的树洞,有些树洞连在一起,形成了一栋大厦。
荔枝成熟的时候,是知了最开心的时候。他们穿着小棕褂,趴在树干上,不停地唱着:知了!知了!他们唱的歌五彩斑斓,很好听。
早晨,他们的歌声像树上的荔枝,火红,热情。
中午,太阳晒得树叶都打蔫了,他们还在唱,像清凉清凉的清风,拂过了我的脸,也吹进了我的心田。
晚上,他们的歌声带着荔枝的甜香,飘着晚霞的云彩,伴着二胡的旋律。
荔枝园的旁边,有一片大草坪,那里是虫虫们的乐园。蚯蚓在钻地洞,螳螂在打猎你看,他们多欢乐啊!
虫虫们在这里生活、游乐、歌唱和工作,这里是他们的天堂。
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 第十二篇
岭南荔枝,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赞叹过啊。苏东坡能一日啖三百颗而不觉其厌;杨贵妃一笑倾城只因"荔枝来";著名作家肖复兴也写到"剥开薄薄的皮儿,露出一张汗津津的小脸,仿佛跑了多远的路才来到这儿",多么俏皮而又显得多么珍贵啊。然而对于长在岭南的我,荔枝并不陌生,也不稀奇,饕餮荔枝是夏日一个固定的节目。
当知了开始歌唱时,我就知道,荔枝快要熟了。初夏,荔枝刚刚上市,深红的果壳带着翠绿,有点刺手,有点湿润,充满生气。这时候,妈妈会在买菜时顺道称上一两斤来尝尝鲜。一般初上市的荔枝还不够甜,带着点酸劲,就像久违的老朋友又一次重逢,初夏的荔枝有股再见时的新鲜。这个时节的荔枝,像爷爷说的"还不到气候",它只能算是饭前汤品,先勾起你的食欲。
炎热的夏天,万里无云,火辣辣的太阳烫得荔枝的小脸越发红了。荔枝的盛季到了,一到市场上,到处都有荔枝卖,一筐一筐,一车一车,吆喝声远远近近,真像热闹的节日。在小街小巷,那些从自家果林摘荔枝来卖的山里人也不断地吆喝着"卖荔枝呀,皮薄核儿小,黑叶哩(一个荔枝品种)"。他们的叫卖声使我想起《荔枝颂》,艺术源于生活,著名粤曲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的一曲《荔枝颂》响遍大江南北,那一声"卖荔枝"的深情至今难忘。
小时候,家里算是一个大家庭。人数多,买的荔枝也多。爷爷喜欢在盛季时买荔枝,不仅价格便宜,质量也好,爷爷到市场上去,直接招呼运着大车荔枝的果农买。等爷爷讲完价,付了钱,我们堂姐弟几个人便抬着一筐荔枝回家了。回到家里,把荔枝往厅上一放,大家围个圈坐下来,一起开动,剥呀,吃呀,那叫一个畅快。
尽管人多,一筐荔枝到底买多了,于是等大家吃饱了,便开始做另一件事情:泡荔枝酒。我们将吃剩下的荔枝剥了皮儿,装到透明的玻璃缸里,浇上白米酒,密封,再找个阴凉的地方储存起来。从夏至冬,米酒浸透了荔枝,荔枝的汁液交融到白酒中,随着时间移动,果酒悄悄地发酵,到了冬天,荔枝酒就可以喝了。在爷爷倒酒喝时,要上一颗泡了酒的荔枝,这时酒荔枝已经失去了玲珑剔透的生气了,它变成了暗沉的棕色。一咬,果肉成了渣,挤出的是酒的辣味,还有被封存了一季的果香,撩拨着味蕾,燃烧着胃。
对于小时夏天的回忆,是甜甜的荔枝和长长地暑假,喜欢夏天,喜欢荔枝,到底是喜欢热烈甜蜜的东西,喜欢关于"吃"的美好记忆。荔枝积蓄了一季的力量,才把甘甜献给我们,它们是跑过了多长的时间才把果实由苦涩变为甘甜?
荔枝的盛季过后,似乎夏天也少了几分热烈的气息,不过也总有一两个来吆喝的,在小巷里听着感觉悠长,悠长……
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 第十三篇
我想大家都知道莆田的三大名果:桂圆、荔枝、枇杷。他们各有各的特色,可我偏爱荔枝。
荔枝是球形或或卵形,像荸荠一样大小,只是全身长满了"鸡皮疙瘩"。
还没成熟的荔枝皮是青色的,随后由浅红色变成紫色。如果你把还没成熟的荔枝剥开,咬一口,酸溜溜的,吃在嘴里,酸在脸上。
成熟的荔枝,是深红的,把它放在鼻子下嗅一嗅,一股诱人的香气便渗入肺腑之中了。你轻轻地剥开荔枝皮,就会看见从荔枝皮里钻出一颗饱满、晶莹、雪白的荔枝的果肉,就像一个从被子里探出脑袋的娃娃。你轻轻地咬一口,会感觉到一丝甘甜从你的嘴一直流到你的心田。
在炎热的夏季,人们通常用西瓜来解渴,其实把荔枝拿去冰冻,过了一两天再拿出来,味道也不错。那是皮变得硬邦邦的,不像平时那么好剥。当你剥开皮,咬一口,会感到牙齿要冻掉了,但是随后你会感到很凉爽,很清新,吃了还想吃。
如果你夏季刚好来到莆田,我一定请你吃香甜可口的荔枝。
我爱家乡的荔枝,更爱我的家乡!
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 第十四篇
我的故乡在广东,我爱故乡的荔枝,我爱故乡的荔枝。
细雨如丝,一棵棵高大的荔枝树吮吸着春天的甘露。它们伸展着四季常绿的枝条。
夏天来了,荔枝熟了,远看就像一个个红灯笼挂在树上。
荔枝圆圆的,遍身生着一些小疙瘩,只要你轻轻一摸,就会扎起手来。
荔枝先是浅绿色的,然后是绿中带红,最后全部都红了。
只要你剥开红色的外壳,你就可以看见一层雪白的晶莹剔透的果肉,吃上一口,让人觉得像喝了蜜糖一样,我真是越吃越爱吃呀!吃完了肉你就可以看见一个褐色的核。
据说"一个荔枝三把火"可真有此事呀,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吃荔枝吃得太多,发现咽喉又肿又疼。现在我才知道荔枝虽然好吃,但是吃多了会上火的。
啊,我爱你,故乡的荔枝!
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 第十五篇
我喜爱娇艳欲滴的草莓、爽脆清甜的西瓜、软糯可口的榴莲,但是最喜欢的还是那香香甜甜的荔枝。
你瞧,圆滚滚的它身披着青红相间铠甲,威风凛凛。又像个小刺猬,在桌上滚来滚去,调皮可爱。拿在手上,你不禁感觉会有些微微的疼痛,有时候用力握着还会留下小红印。
当你迫不及待为它脱下铠甲的时候,只听见"咔嚓"一声,晶莹剔透的果肉一点一点探出头来,好似是羞答答的小女孩。我忽然想到了明朝丘浚的《咏荔枝》——"世间珍果更无加,玉雪肌肤罩绛纱"真是说的一点也不错,坚硬多刺的盔甲里竟然藏着这样一个绝世美人!而且当荔枝被剥开的一刹那,一阵甜香味儿在空中弥漫开来,我忍不住用力多嗅几下,全身心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再轻轻一咬,果肉冰冰凉凉,柔柔嫩嫩。甜甜的汁水也在我的口齿间爆开,充溢着幸福的味道。也难怪苏东坡会感叹"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唐明皇会派"一骑红尘"让"妃子笑"……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水果——荔枝,你喜欢吗?
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 第十六篇
我的家乡在福建泉州,我爱家乡的山山水水,更爱家乡的特产——荔枝。
在我外公家的后院,有一棵树龄50多岁的荔枝树,它枝繁叶茂,四季常青,枝干上结的果实就是荔枝。荔枝还没成熟时,个头小小的,一脸青涩的感觉。一到夏天,荔枝就渐渐熟透了,聚在一起压弯了树枝。这时,外公会带上工具去采摘,我每次都跟在他身后,眼巴巴地看着一筐筐的荔枝,口水直流,恨不得马上把它们都吃掉。
荔枝看上去感觉像待嫁的小姑娘,外壳鲜红艳丽,有的还带着几分青绿的羞涩,但掰开来,果肉却是白白嫩嫩、晶莹剔透、清香多汁,棕黑色的果核在圆润的果肉中若隐若现。轻轻咬一口,甘甜的汁液就如同调皮的孩子似的,在我嘴里上蹿下跳,慢慢充盈整个口腔。吐出果核,把果肉和汁液送进肚子,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甘甜直沁心扉,让我整个人顿时沉浸在荔枝的世界中,无法自拔。
"口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的《食荔枝》令我印象深刻,但每次多吃几颗,第二天就容易咳嗽上火。原来,荔枝含糖量高,再好吃我也只能克制住自己,无法像先贤那样"一次爱个够"。
我爱家乡,更爱家乡的荔枝,永远也爱不完!
小学生作文深圳的荔枝 第十七篇
今天,妈妈买了几串又大又红的新鲜荔枝,我左看看,又看看,瞧个不停。
只见成熟的荔枝,大多是深红或紫红色的,从远处看去,像一颗颗诱人的"珊瑚珠"。那一串串的荔枝,宛好一簇簇红宝石,在金灿灿的阳光下流动,闪烁着令人眼迷的光。
我从中摘下一颗荔枝,顿时一股浓郁的香味直沁人心脾。小心翼翼地剥开荔枝那华丽的红装,随即露出了一层粉红色的薄膜,那薄漠紧紧地包裹着丰满的果肉,宛若一盏盏透明的红灯笼.一闻,啊,那香甜甜的味儿直冲进喉咙,搅得喉咙怪痒痒的。我迫不及待地剥开那一层薄膜,啊!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颗不断往外溢着果汁的白嫩嫩的荔枝肉,简直像一颗透明晶莹的珍珠。
吃完了荔枝,只剩下荔枝核了,它圆圆的,有荸荠一样大小,只是遍身长满了疙瘩。
荔枝,荔枝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查看更多
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思维导图
 U633687664
U633687664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10b9a8a2dd2fb4593f8130ef16c320fc

9.战斗的基督教思维导图
 U582679646
U582679646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战斗的基督教》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战斗的基督教》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33d168acd0cd9f767f809c7a5df86e3a

相似思维导图模版
首页
我的文件
我的团队
个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