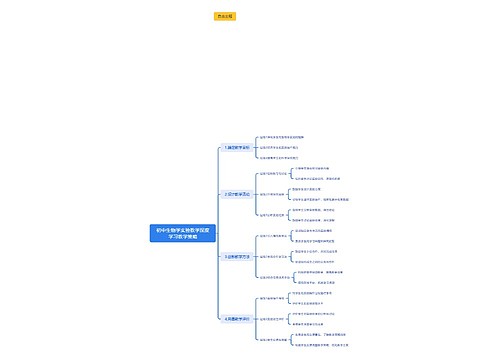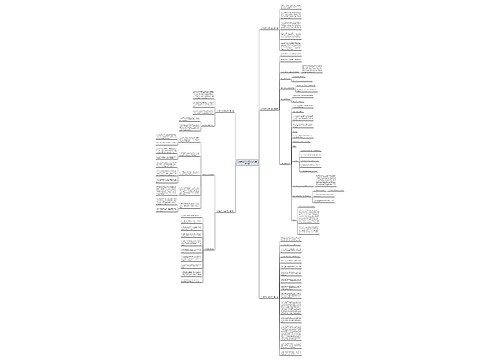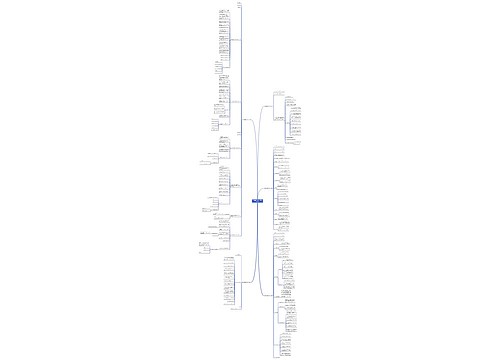初一精选美文(摘抄美文 初中生)思维导图
轻涟低眉
2023-05-08

篇一、归来秋来了,望着雁阵轻盈地掠过天空,我心中却填满了忧伤。我老了,枯稿得一触即碎。我惊恐地感到根部的疏松,仿佛随时要被风斩脱枝系。看着同伴们没入沙沙之声,纷纷扬扬地逝去,哀愁就涌上全身的每处经脉,恍若淹没在悲伤与死亡的阴影里。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初一精选美文(摘抄美文 初中生)》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初一精选美文(摘抄美文 初中生)》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24ed5b1be5de86f31dad51fac127137e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新教材 新变化思维导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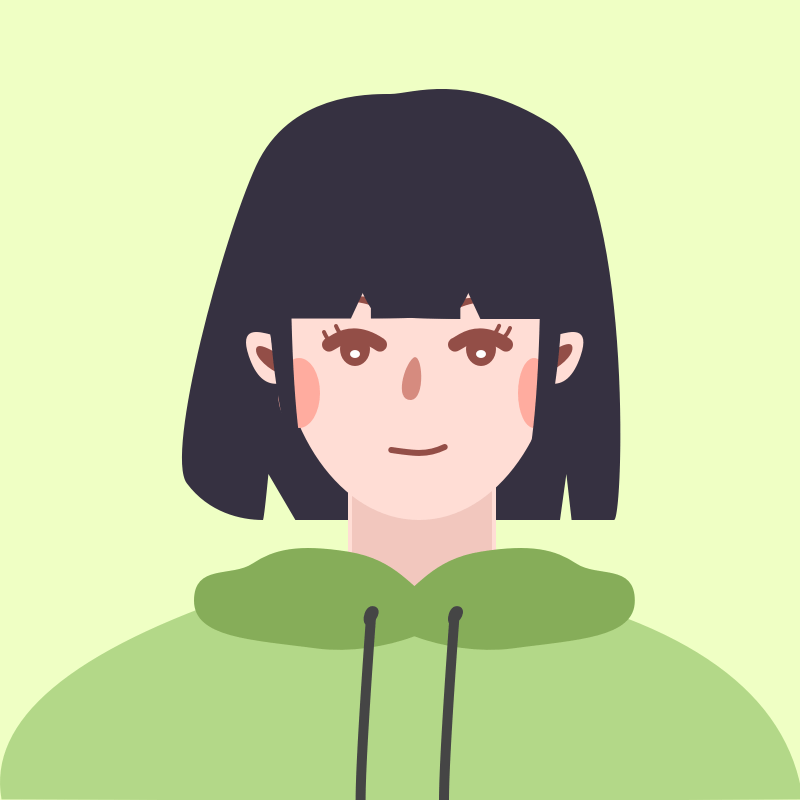 U541085537
U541085537树图思维导图提供《新教材 新变化》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新教材 新变化》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fd32830c00343a270a1024879f41343d

初中生物学实验教学深度学习教学策略思维导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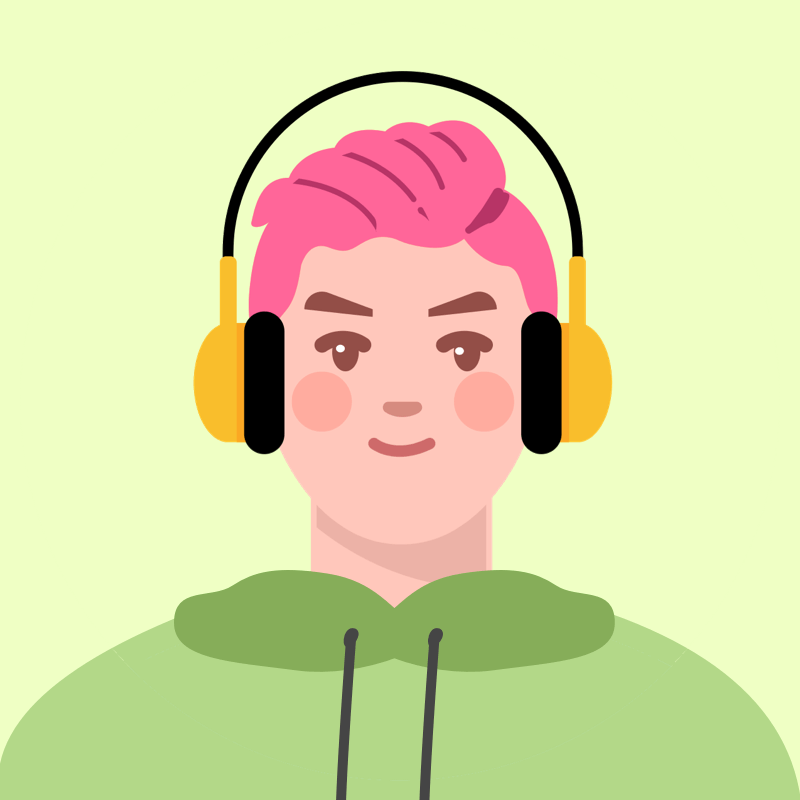 U860461431
U860461431树图思维导图提供《初中生物学实验教学深度学习教学策略》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初中生物学实验教学深度学习教学策略》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9b0de4118b1899a4536b2bef54350e9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