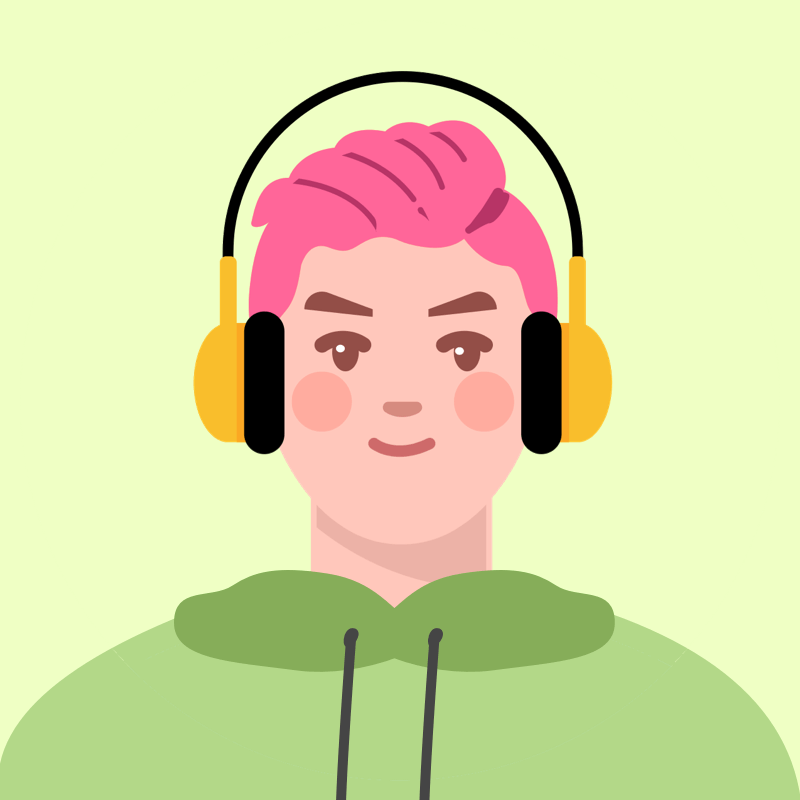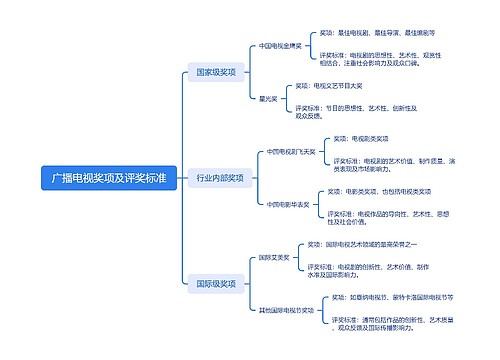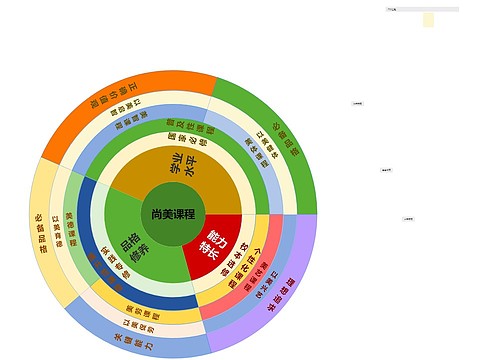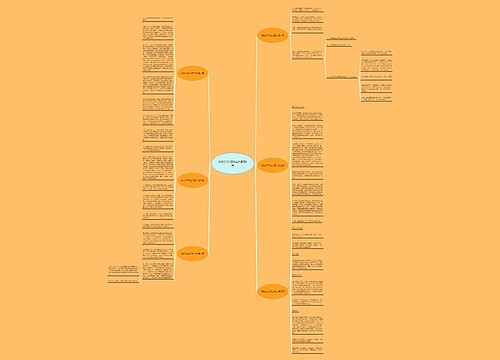劳动一词,有时含有"为生计所迫"的勉强;然而,劳动的内涵和维度却是非常宽延的,无边无垠。劳动,需要有时间的渗透,有行动的支撑,有心境的参与……有时很苦,很磨人;有时很美,很自在。
当一个人全身心投入并沉醉在劳动之中的时候,美,就现身了。
青少年时,我跟着我爹下田锄地,曾领略过劳动的一二奥妙。那时,面对一大块绿油油的田地,我先是激情万丈,想着急速完工,赶快脱离那种单调和重复。于是,手下三扒两扒,吭哧吭哧,就跑到前面去了。爹的动作却慢悠悠不温不火。我爹说,一上来就把劲儿用展,坚持不长哩。他话说完没多久,我已露怯,臂软腿酸心发慌,做不动了。爹说,看,这就是典型的五分钟热度。越是简单的活儿,越需要耐心。靠三分钟急劲儿,啥事儿都做不妥。
我爹边说,边徐徐地,稳稳地,将土层划松,将杂草剔除,将禾苗儿扶正。不紧不慢,似有坐禅入定的意思。一亩来地,他始终如此,像在完成一篇文气紧凑的美文华章。
我坐在田塍上,暗暗把我锄过的地垄和爹锄过的做比较,哎呀,脸红了。眼见我做出的活儿,鸡爪挠过似的,潦潦草草。
那时,我悟出了:在劳动中,耐心、恒心,其实也是一种出众的才干。
我爹只是个老农民,说才干,似乎是高抬他;他手中的农具,也都愣头愣脑的,笨。可他整理出来的田地却细致有章法,麦田、菜畦……平展展的,没有一个坑洼;土畦又细又匀,看不见一个土坷垃。他种的每块地都像被剪裁过,棱是棱,角是角,站在地头望,美不胜收,让人情不自禁想起"锦绣江山"这个词语。他那些笨头笨脑的农具,俨然绣花针般灵巧,在田间绣出了最美的画。
我母亲,同样也是一个手里出"好活儿"的人。一日三餐、四季衣服、鸡鸭狗猪小毛驴,都要她去操持。但我娘轻轻松松,抬手就拾掇出了清整的秩序。做家务、下田之外,她还照料着三分小菜园。
懂行的人说,种菜如绣花,是细致活儿。从劳动量说,一亩园十亩田,很累人。但我娘在菜园里,总是很快乐很轻松的模样,虽然多数时候汗水浸湿了她的鬓发。
她把被风雨扑倒的菜苗扶正;给疯长的西红柿打杈;给南瓜、丝瓜牵藤;给蔬菜捉虫。她边做活边跟菜宝宝们说着体己话儿:"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么赖皮呀!都侵了人家豆角架了,好,你在这边爬!不许再窜过来!""呵呵,你这个歪瓜呀,是仿着谁长得这么丑哇?""好了,好了!我把这棵草虱子拔掉了,你大胆往上蹿吧,再没坏蛋揪着你了!""嘿,乖乖!你就甘心受它欺负呀!来,我给你除害!"她把一个大毛虫捉进了瓶子。
跟父亲下田,我觉出一种禅意的宁静;跟母亲种菜,我体会到一种轻松宽畅的愉悦;而当观察木匠姑父的劳动时,我充满了一种对创造力的敬佩。
四姑父上门,就意味着我家要安窗上门、做个箱柜啥的,请他来帮忙。
四姑父把长短不齐、薄厚不一的一堆木头,凝眉审视一番,像构思一篇作品。然后,郑重动手。我常见他骑在板凳上,在木板上推刨子,嚓嚓嚓,一卷卷刨花层层落下,淹没了他穿着解放鞋的双脚。他又拿尺子和墨线盒,在木板上画;有时,乜起一只眼,像打枪时瞄准儿。他的脸上满是凝重,似乎全部的生命热情都铺展在那块板儿上了。
他把七七八八的木头分开,凿眼,刨平,又合住,使它们最终呈现我们渴望的样子。
他干活儿的样子,真叫人难忘:百分百专注,近乎虔诚;周围再嘈杂、喧腾,也搅扰不了他那种静气。
我喜欢观察劳动中的人,那是一个浩瀚无边、自得自足的世界。那种情景的人,最美。而劳动之美,不是肤浅水滑的皮面,而是一种自内而外的温润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