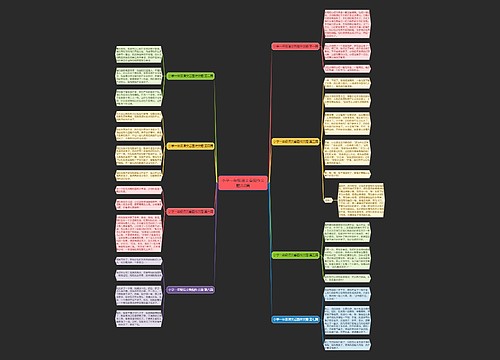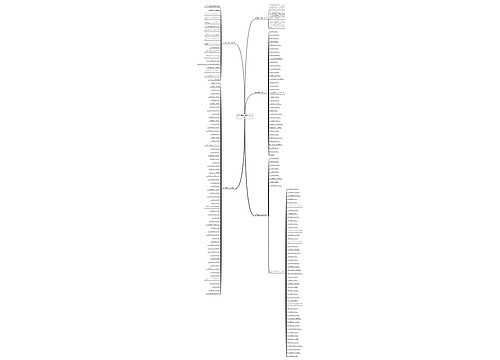风中夹杂着各种草木的清香,更是将窗头的茉莉芬芳暗送入室。 茉莉,应当是一种很平凡的植物了。
它的花色纯白,枝叶没有什么特色,习性也并不娇贵。它只是盛开在江南的万紫千红中的素净的一朵。
人们注意它,大都是因为它的花香。 这实在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花香。
它清新淡雅,幽远沉静,全无甜腻之感,又并不是躲躲闪闪、若隐若现的。宋人有诗云:"一卉能熏一室香",赞的就是茉莉花香,一枝茉莉花就能使一室香气弥漫。
天下有太多的花香。有些彼此相似,于是湮没无闻;有些却被花朵的丰姿所掩盖,因此常常被忽视。
由此看来,茉莉花香是出色的,它不落窠臼;茉莉花香又是幸运的,它与花朵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点评茉莉,说过:"是花皆晓开,此独暮开。
暮开者,使人不得把玩。"诚如此言,茉莉花常常在暮色中静静绽放,夏日夜风穿过厅堂,将茉莉的清香拂遍各个角落。
然而,花虽然在夜幕中开放,却并非像笠翁所说"不得把玩"。站在花前,静静凝望,夜色中的茉莉更添了几许风姿绰约的意味。
刚刚绽放的花朵,颇有些像亭亭玉立的荷花,只不过更小巧玲珑一些。等到花瓣全部张开,花形就不再规则了。
夜色中,光与影在花瓣上描出精致的图形,从不同的角度欣赏,我们就能看到一个独一无二的美。 一朵茉莉花,从绽开到凋落也不过三四天。
微风吹落枝头的花朵,花犹洁白,暗香残留。世上的人们到底是不情愿花谢花飞的。
花瓣终究要化作春泥,而花香却可以保留下来。茉莉香片久负盛名,清淡的茉莉香与清幽的绿茶香融为一体,恰如其分。
其实,两者的清香都出于自然造化,完美的搭配背后,只是一种返璞归真的简约与淡然。 古人赏花,品评之余,总不忘留下几首诗词来寄托情感。
"玉骨冰肌耐暑天,移根远自过江船。山塘日日花成市,园客家家雪满田。
新浴最宜纤手摘,半开偏得美人怜。银床梦醒香何处,只在钗横髻鬓边。"
清代诗人陈学洙的诗将茉莉的形态与种植盛况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还有一个画面,也使我难以忘怀。
《红楼梦》中有一句这样的描写:"迎春又独在花阴下拿着花针穿茉莉花。"这似乎只是一笔淡淡的风景,却让我怦然心动。
我不想、也无法品咂出这句话背后的寓意,就是被这个镜头打动了。画面里,温柔沉默的闺阁少女轻轻柔柔地摘下一朵茉莉花,指间的针线让它继续芬芳散逸。
那一刻,软弱的迎春也终于有了可以让她自己选择的东西。独在花阴下穿茉莉花,这个氛围雅致,优美,入诗入画。
茉莉花在丝线上串成球,大概是要戴在少女的皓腕上,抑或是悬挂在她们的衣襟边的吧?茉莉花的花蒂上恰好有个孔,能穿在簪子上,很是巧妙。《浮生六记》里,女主人公芸娘就曾经把茉莉花簪在发髻里,因为它形似珍珠,溢香消暑,适合为古代女子助妆。
也许,茉莉花与闺阁女子的机缘正是在此。茉莉的植株是矮小的,栽种在花盆里,摆放在窗台前。
闺中女子的天地也是很小的,从镂花窗格里,她们希望看到更大的世界,可惜她们的视野又是那样有限。只有窗前的茉莉,是她们另一种意义上的闺阁伴侣。
江南,有太多茉莉一般的女子。每次读到苏轼的《蝶恋花》,读到那句"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我总会想起茉莉花的娇小倩影。
那是一位坐在秋千上的佳人,那是一位会用针线穿茉莉花的佳人。不过,她不是迎春一般的女子。
毕竟,"墙"是矮墙,青砖黛瓦;墙内的女子,只是江南的小家碧玉,而不是金陵古都中的大家闺秀。佳人的笑声传到了墙外,但也仅止于此;最终,依旧是"笑渐不闻声渐悄",佳人还是走下了秋千,回到了绣楼;依旧,只有窗前的茉莉花轻轻盛开着。
对镜理妆时,茉莉为佳人增得了一分颜色,也在默默地分担着佳人的寂寞与闺怨,更承载着江南女子细腻温润的古典情怀。"银床梦醒香何处,只在钗横髻鬓边",诗句的精致让人向往那种意境,可是,那份哀怨和孤独,到底还是会从茉莉的幽香中一丝一丝地透出来。
记得在一个水乡小镇游玩的时候,我曾经泛舟河上。船头是身着蓝印花布短衫的船娘。
水波一轮一轮,柔柔地荡了开去,船娘的歌声也飘了过来。那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江南小调《茉莉花》。
曲子并不长,四句歌词,起承转合,旋律委婉,波动流畅。这首曲子,在中国早已是家喻户晓,更通过歌剧中的音符飘到了国外,几乎成为了中国音乐在国际上的首席代表。
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歌唱家们总喜欢在重大场合上演唱这首歌,用美声唱法,用民族唱法,把这首江南小调演绎得高了好几个八度,凭空地厚重了许多。其实,这又何苦来呢?歌剧与小调,毕竟是不同的;这最初的旋律,也不是为了让歌唱家们展示高音而创作的。
倘若没有约翰·贝罗记下了《茉莉花》的曲调并带回欧洲,倘若不是普契尼在歌剧《图兰朵》中运用了《茉莉花》的元素,也许至今,这首曲子还是单纯如初,与流传在江南的千百首民歌没有什么区别。可是现在,它的地位显然不同了。
上世纪90年代,江苏省的南京、盐城等城市争相站出来说是《茉莉花》的发源地。最终,这首民歌花落扬州。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