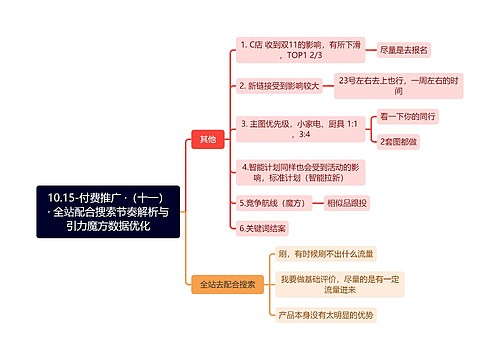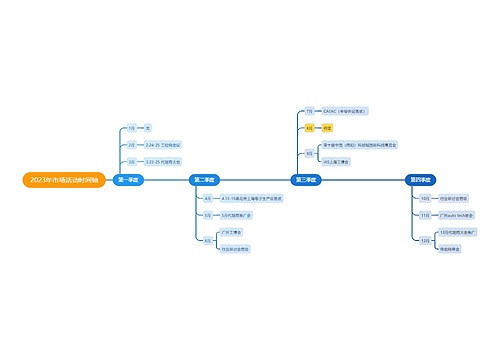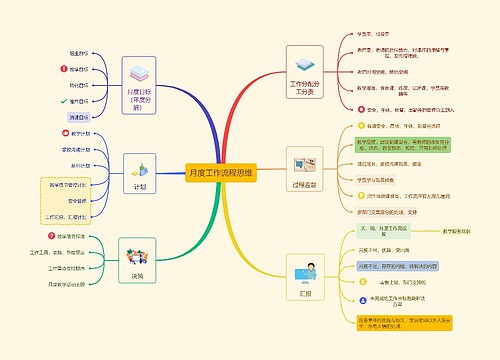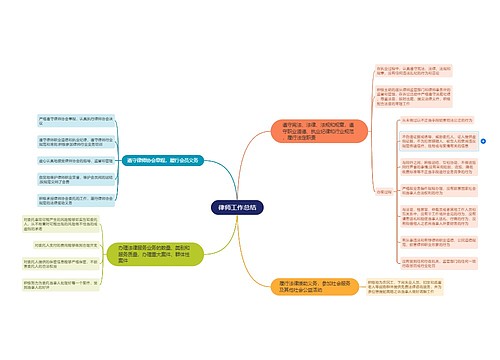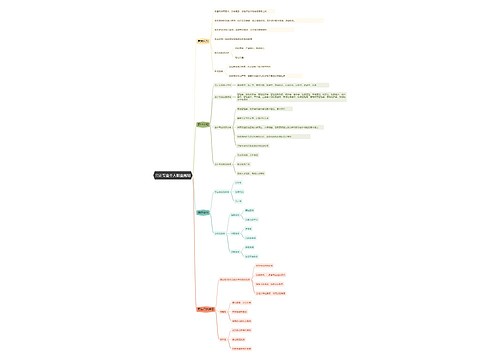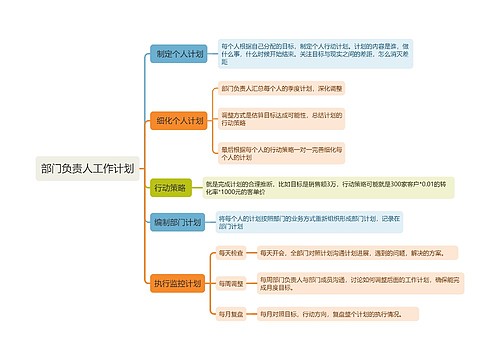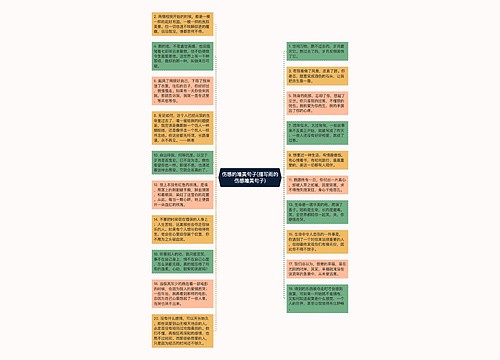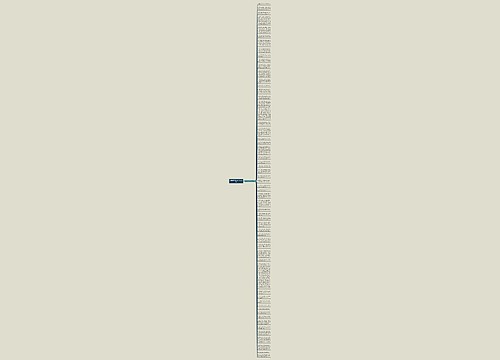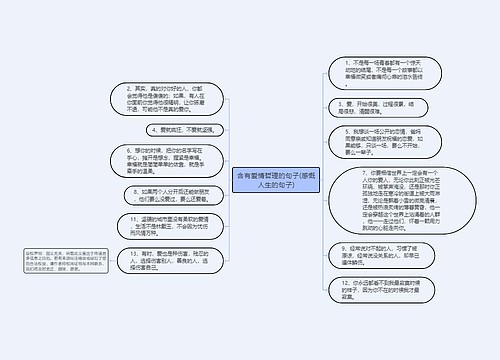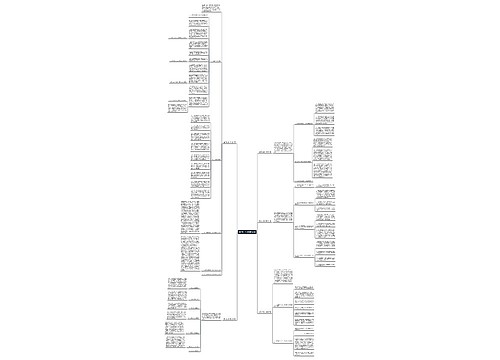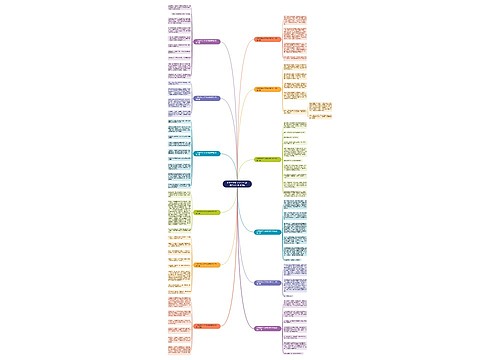傅聪:他是一个在中国最优秀的传统中植根非常深的知识分子(我说的是最优秀的传统,从屈原一直到现在的传统),同时又是"五四"的觉醒一代。...我爸爸责己责人都非常严,是个非常严谨的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有东方文化的根,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从西方文化中来的,他的那种科学态度,很强的逻辑性,讲原则,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优点。他在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时说过,他受这本书影响很大。罗曼·罗兰作为一个欧洲人,有这么个理想,他希望能够把德国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两个民族的文化取长补短,创造一个更灿烂的文化。我爸爸一辈子追求的就是希望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间取长补短,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更灿烂的全人类的文化。
傅聪将中国诗词的格律、意境、文化观念运用于钢琴演奏之中,成为以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音乐进行人文阐释的践行者。他经常用中国古典诗词来诠释西方音乐,比如认为德彪西的音乐更多的是王国维讲的"无我之境"那种"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的境界,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美学。他的演奏中蕴涵对中国传统艺术境界的把握,在国际钢琴界赢得"钢琴诗人"的美名。
傅聪说:"我觉得山水画是人和自然的融合,就是天人合一,完全是人把山水的精神都化到人的心里去了,人把山水人化了。山水好像又有人的精神在那儿。"在他眼里,肖邦音乐里面包含中国画,特别是中国山水画里的线条艺术,尤其是黄宾虹山水画里的那种化境、自由自在的线条艺术。他说:"一般人谈肖邦只晓得听旋律,肖邦音乐的旋律是很美,可是在旋律之外大家往往忽略掉其他声部的旋律。肖邦音乐是上头有个美丽的线条,无孔不人,有很多表现。"为什么都说肖邦是"钢琴诗人"?傅聪认为,肖邦的音乐最接近于诗,他第一次接触《大调夜曲》作品六十二号时,觉得最后那一段是"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傅聪在钢琴演奏中将中国古典诗词中有关音节的起伏、音韵及情绪的变化同西方的钢琴作品联系起来,以中国古典诗词诠释西方钢琴音乐的韵律美,呈现独特的阐释方式。傅聪在演奏德彪西的《西风说的是什么》这首作品时,将钢琴曲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联系起来,他这样谈自己演奏中的体会:"杜甫那首诗一开始‘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然后是艺术家不可或缺的humannity(人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最后是好几个fortissimo(极强)——‘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何等伟大的心灵!"他借鉴此诗结尾处的韵律特征进行演奏,使之具有强烈的情感特征。
他也曾这样阐释莫扎特《回旋曲》的演奏心得:"完全是李后主《清平乐》中的‘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句‘更行更远还生’就是这首《回旋曲》主题。"他在演奏中将《清平乐》长短句组合格律的变化与《回旋曲》的节奏与重音规律结合,并借鉴诗词所蕴含的情感因素,使之彰显中国古典诗词所遵循的美学原则。
赫尔曼·黑塞在电台里听到傅聪演奏的肖邦,当即被震惊。他立即写出一封公开信《致一位音乐家》:"我所听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肖邦...他的演奏如魅如幻,在"道"的精神引领下,由一只稳健沉着、从容不迫的手所操纵,就如古老中国的画家一般,这些画家在书写及作画时,以毛笔挥洒自如,迹近吾人在极乐时刻所经历的感觉。此时你心有所悟,自觉正进入一个了解字宙真谛及生命意义的境界。"
很多欧洲人惊叹为何肖邦转世会是中国人。对此傅聪曾解释道:"恰恰是中国诗词滋养了我,才使我有了诗人的气质,也才得以被人们冠以肖邦再世的名号。"这与其父傅雷的教育观念密不可分。傅聪年幼时,父亲亲自编写文学教材教授他,还建议他要经常阅读古代散文。傅聪出国后,傅雷经常将包括中国古典诗词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寄给他,同时以书信方式对儿子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引导。
傅聪把肖邦的钢琴曲演奏到极致,名振音乐界。1954年,傅聪在音乐家肖邦的故乡跟"波兰最好的肖邦研究学者"杰维茨基学习钢琴。1955年,他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得第三名与《玛祖卡》最佳演奏奖后,"有波兰性格的中国人""中国籍的波兰人"成为西方音乐界对傅聪的第一印象。自此,他的演奏事业与肖邦产生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傅聪的观念里,肖邦在音乐史上的地位不但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没有肖邦,浪漫乐派就不够完整。
傅聪怀着虔诚的敬意,来到肖邦故居。那里,已经成了肖邦纪念馆。他静静肃立在肖邦画像前,久久凝视肖邦瘦削、忧郁的脸,默默仰望着他的目光。肖邦故居有两架钢琴,一架是古老的"普莱埃尔式"钢琴,那是19世纪的钢琴技师普莱埃尔为肖邦制造的,这个珍贵的纪念物受到精心保护,参观者只能站在栏杆外看。另一架是现代钢琴,供参观者在那弹奏肖邦的乐曲。傅聪坐到琴前,怀着对肖邦的崇敬之情,弹起肖邦的作品。他的琴声马上引起注意。波兰人用惊奇目光注视他:一个东方人,一个中国人,怎么会有"肖邦的灵魂"?怎么会在琴声中反映出"肖邦精神的真谛"?
傅聪在波兰多次演奏肖邦作品,得到波兰研究肖邦专家重视。波兰政府正式向xxx提出,邀请傅聪参加1955年2月至3月在华沙举行的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1954年8月,他被政府派遣到波兰,在波兰的"肖邦权威"杰维茨基教授亲自指导下学习。教授个子瘦小,头发花白,稍有点儿驼背,表情总是很严肃。他倾心指导这个中国学生,为教好傅聪,他甚至特意训练他的英语。如同傅聪在信中所说:"(杰维茨基)作为教授,在风格上,在对每个作曲家的每个时期的作品的理解上,在世界上要算是有数的权威了。""他们对我期望非常高,我绝不能辜负他们,而且也是自己和国家的体面,因此我得加倍用功。我每天练八小时以上,他们每人不过五小时。我来得太晚,准备得太晚,技术根基又差,不拼命是绝对不行的。"
那时候的傅聪"浑身都是青春的火花,青春的鲜艳,青春的生命、才华",他确实处于"一生之中的黄金时代"!
当时,五年一度的国际肖邦钢琴比赛离开幕之日越近,傅聪练琴越勤。他的手指尖弹痛了,就包上橡皮膏弹。深夜,他躺在床上,还在那里琢磨肖邦作品的章节句读。
傅聪以诠释肖邦作品成就最大,他的人生经历也与肖邦的有相似之处。肖邦年轻时,因祖国波兰遭到入侵而被迫流亡外国,终其一生都未能回国。而傅聪年轻时出走英国,当他再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已是20余年后。他在肖邦音乐里,寄托了对故土无可奈何的乡愁。

 U237990653
U237990653
 U249128194
U249128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