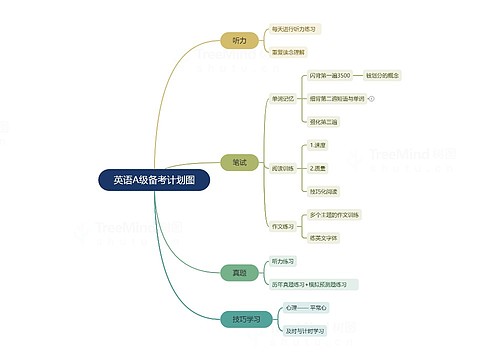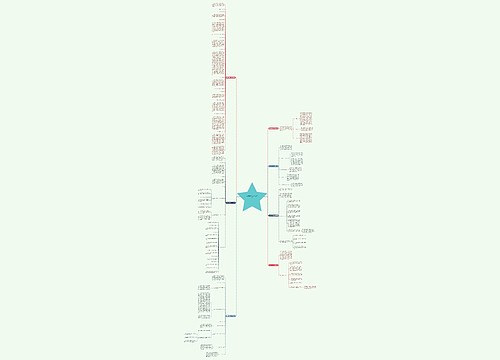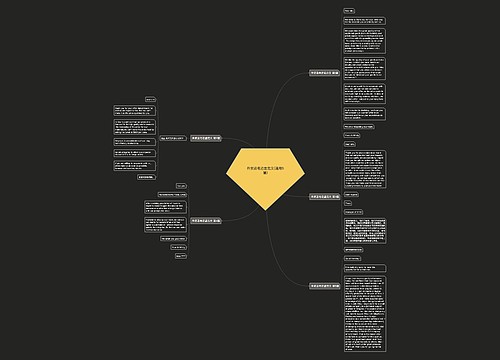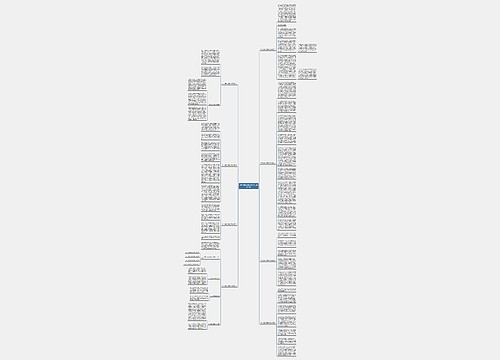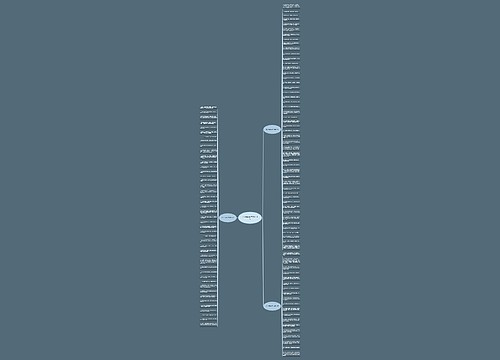西方有一位诗人写过这样一句诗:"我想描述一束光,它来自我的内心。"我很喜欢这句诗。
与我而言,这束诞生自内心的光有可能是我们体内一只奔跑的蚂蚁、一只飞翔的蝴蝶,甚至是一面为我们呐喊助威的锣鼓。
喧闹的时候、寂寞的时候、孤独的时候、快乐幸福的时候,很多时候,甚至在尘世的舞台上得意忘形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的体内有一只虫子,一只蚂蚁一样在我们骨头里、血管里、筋脉里奔跑的虫子,它在寻觅灵魂的穴位,撕咬我们最敏感脆弱那根神经。
在得意忘形的时候,蚂蚁的撕咬让我头脑清醒。我总想拿出笔或者像一只卧在电脑键盘上的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安静地敲一些文字。以这些从生活的煤层里掘出的文字为拐杖,直立行走,向着阳光深处或者鲜花盛开的地方走去。因为有了"写"和"敲"这两个微小的动作,我平凡的生活不再像一只破了洞的袜子一样空洞。而我思想的足已经远行,不再担心行走在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上还是行走在万丈坦途间。
我们常常忽略常识,又被常识欺骗。不多的人生经验晦涩地告诉我:即便前面是万丈坦途也要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即便是荆棘丛生的小道,也要保持举重若轻的从容自信。因为只有最熟悉的路上我们最容易摔跟头,然后鼻青脸肿地说:原来井底之上的天并不是圆的。
世界被夜色笼罩的时候,我们可能睡去,但体内的蚂蚁一直不曾停止奔跑。我们的肉体是蚂蚁奔跑的泥土,我们的气息和语言很可能就是它奔跑时卷起的灰尘。我们的胸怀就是蝴蝶飞舞的天空,我们的某个穴位就是蚂蚁的家。它们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我们的敌人。因为我们心存善意和信仰,它有可能在我们的某个穴位打开一扇门,让灵魂出窍,抵达一个安静而又高远的境界;如果我们内心汹涌太多的欲念,它们有可能停止奔跑,在我们某个致命的补位掘开一个漏洞,使灵魂的堤坝失守,溃于蚁穴。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只能在喧闹中冷静坚守,就好比在污泥塘里亭亭玉立的荷花一样,身陷泥塘,心却高高在上,不染纤尘坚守骨子里的那种高洁和优雅,在白天黑夜里,在清风明月下,在喧闹纷扰中,默默地放开喉咙,为这个世界释放出灵魂的芬芳。
不要过多的赞美,也不要太多的瞩目,即便没有赞美和瞩目,那只卑微的蚂蚁有时候肉眼看不见,它只是悄悄地用它纤细瘦弱的腿脚敲打我们的骨骼,当我们的骨骼坚韧得足以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时,它有可能长上翅膀,大鹏一样飞出它的泥土地,拉长我们的影子,拔高我们的脖颈,让我们清楚地看见原来的我们是那么渺小。
为了让一只奔跑的蚂蚁变成一只展翅的大鹏,我们没有理由停止让心灵奔跑和飞翔的信仰。(马国福)
一位名叫薛瓦勒的乡村邮差每天徒步奔走在乡村之间。有一天,他在崎岖的山路上被一块石头绊倒了。
他起身,拍拍身上的尘土。准备再走,可是他发现绊倒他的那块石头的样子十分奇异。他拾起那块石头,左看右看,便有些爱不释手了。
于是,他把那块石头放在了自己的邮包里。村子里的人看到他的邮包里除了信之外,还有一块沉重的石头,感到很奇怪,好意地劝他:"把它扔了,你每天要走那么多路,这可是个不小的负担。"
他却取出那块石头,炫耀着说:"你们谁见过这样美丽的石头?"
人们都笑了,说:"这样的石头山上到处都是,够你捡一辈子的。"
他回家后疲惫地睡在床上,想着山上到处都是美丽的石头,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用这样美丽的石头建造一座城堡,那将会多么迷人。
于是,他每天在送信的途中寻找石头,每天总是带回一块,不久,他便收集了一大堆奇形怪状的石头,但建造城堡还远远不够。
于是,他开始推着独轮车送信,只要发现他中意的石头都会往独轮车上装。
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过上一天安闲的日子。白天他是一个邮差和一个运送石头的苦力,晚上他又是一个建筑师,他按照自己天马行空的思维来垒造自己的城堡。
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不停地寻找石头,运输石头,堆积石头。在他的偏僻住处,出现了许多错落有致的城堡,当地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个性格偏执沉默不语的邮差,在干一些如同小孩子筑沙堡的游戏。
1905年,法国一家报纸的记者偶然发现了这群低矮的城堡,这里的风景和城堡的建筑格局令他叹为观止。他为此写了一篇介绍薛瓦勒的文章,文章刊出后,薛瓦勒迅速成为新闻人物。许多人都慕名前来参观城堡,连当时最有声望的毕加索也专程参观了薛瓦勒的建筑。
现在,这个城堡成为法国最著名的风景旅游点,它的名字就叫做"邮差薛瓦勒之理想宫"。
在城堡的石块上,薛瓦勒当年的许多刻痕还清晰可见,有一句就刻在入口处一块石头上:"我想知道一块有了愿望的石头能走多远。"
据说,这就是那块当年绊倒过薛瓦勒的石头。(陆勇强)
我参与的网站"美华论坛",成立于2004年底,画家南亭先生的儿子,才七八岁,也常来发表绘画和作文,很受大家喜欢。这位"灵隽小友",如今上初中了,前几天在网上发表的一辑照片,是少年友情的实录,在班里的同学们合照下有一句:"时间是不等人的。"这个年纪,按苏东坡的说法,日子最难打发——"日长如少年",谁有功夫叹息光阴易逝,年华不再?唯独这位天份甚高的初中生,提前窥见时间的无情。
不过,我要郑重地对少年说:时间是等人的,不要担心。时间等你,也等我,等全世界的生灵。时间等在你之前,等在你之后;等在显意识,等在无意识;等在有限,等在无限。学校里的老式挂钟,钟摆就是你的脚步;家里的电子表,即使你在沉睡,液晶数字也显示你梦里的呼吸。一如古老的沙漏,每一颗细沙都是当时活泼的生命。时间不能离开你,你就是它,它就是你。你"被"时间长大,时间被你证明。没有了你,何来"你的"时间?你不久将发育,喉结变大,童声变粗,骨骼身个像夏季的水稻般拔节。没有时间,你如何完成这样的蜕变?"你的时间"是你生命全部的外延和内涵,你的一生为"你的时间"做"填空"的作业。
我们从小就接受了这样教诲:"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明日复明日,万事成蹉跎","一寸光阴一分金,千金难买寸光阴",基调是时间的冷酷。其实,时间和人的关系,并不是"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无所谓彼此,时间就是人,人就是时间。你是"这样"的人,就有"这样"的时间。特定的时间,成就特定的人。所以,没有"等"的问题。明了这一层关系后,你可能认为,既然时间并非咄咄逼人的怪兽,那么用功干嘛?多打电子游戏吧!不过,你须再站高一点看。
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命题:时间即生命。比如说,某同学学习足够刻苦,两年的课业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这过程,并不意味多少时间给"节约"出来,而是激发出时间的能量,时间的长度没变,但质量和密度产生飞跃。微波不兴的死水是水,"飞流直下三千尺"也是。对时间的任何损伤,是对自己的损伤。比如说,你本来要跟父母去看望住院的外祖母,但你躲在网吧,不听电话,错过了,老人在病床上苦苦盼望你,最后失望地叹气。你不要把过错推给时间。人生道路上一个闪失,就是"你的时间"中一个伤痕。将来,你进入社会,在竞争激烈的职场,无论受雇于人,还是自行创业(你现在已画出很不错的国画,看得出你富于独创性,成年后可能当上艺术家,即所谓"自由职业者"),在那个"黄金时段",你最关注的该是"机遇",也就是"遇上机会"。说来说去,又是"时间"的事,太早,"强拧的瓜不甜";太晚,"挑水的回头——过景(井)了",我这么说,你别以为抓到反驳的理由——看,时间要么是搭档,要么是对手,怎么可能和我合体?我说,机遇仍旧是你自己的事,你从前所准备的,所损坏的,所期待的,都在造因,所谓"关键时刻",乃是时间(也就是你自己)作出阶段性的总结。
明了你就是时间,极为紧要。没有"生不逢时"的问题,只有如何创造自我的问题;没有"时不我待"的问题,只有按自己的图样打造生命的问题;没有朽与不朽的身后事,只有你对自己的责任感和承受力。
聪明的中学生,愿你的生命(也就是你的时间),这最伟大的财富,你善加运用,到最后,花光了,你就进入永恒的虚无。这以后,时间当然在,不复属于你就是了。 (刘荒田)

 U281619454
U28161945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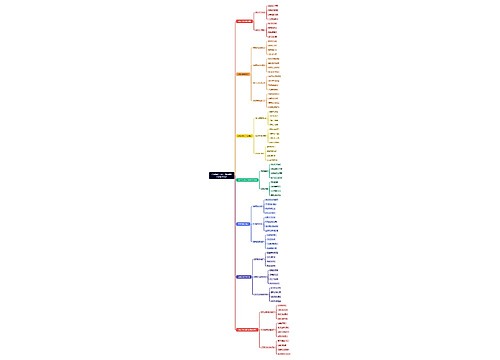
 斯内普的洗发水
斯内普的洗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