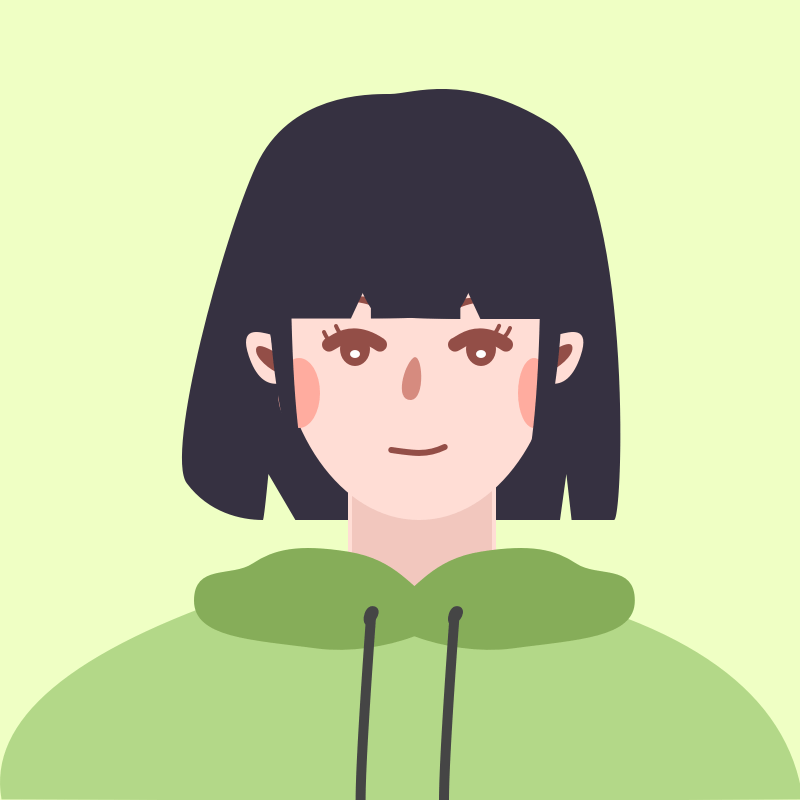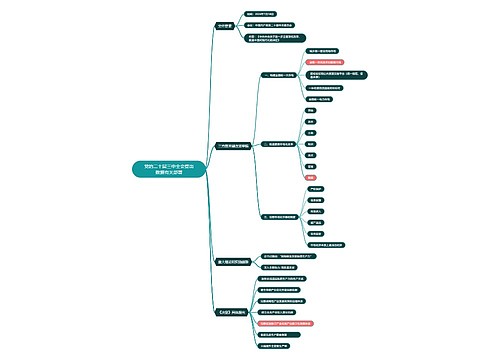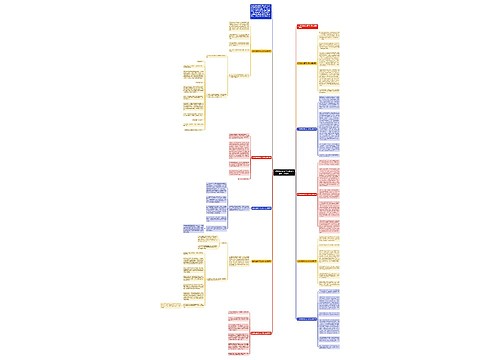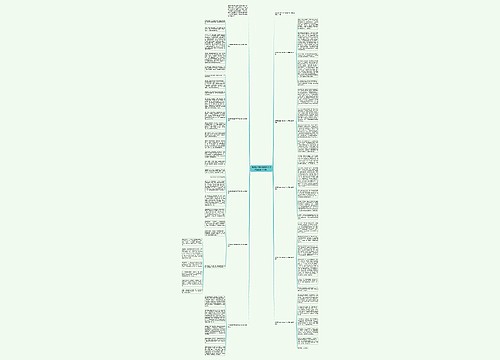对于中国人来说,除夕是个特别隆重的日子!而在我看来,父亲对于除夕的礼拂似乎比一般人家显得更庄重而虔诚!
我从小就会在大年三十这天,跟在父亲身后,看父亲贴春联,贴喜钱,贴年画。贴好正屋贴厨房,贴好门框贴窗框,像个小跟屁虫似的。
父亲脾气暴躁,可是在除夕这天却特别温和,他会让我看他贴在大门上的一对春联是否一样高,也会教我念春联内容,还会抱着我让我看年画。
大红的春联、楹联、喜钱把赭褐色的大门、窗框装扮得喜庆盈盈,各种年画盖住了灰朴朴的墙面,显得雅致祥和。父亲净身净面净手后,点燃了一对红烛,烛烟升腾,蜡香四溢,又虔诚地点燃三炷香,举过头顶小心地插在香炉里,香烟袅袅娜娜,檀香缭绕。端坐在案几上的观音菩萨、福禄寿财菩萨、弥勒佛,享受着人间烟火,外面飘飞的雪花不时旋进屋子里,显得既庄严又神秘!
一家子排好队,从父亲开始,然后是母亲、三个姐姐、哥哥、我,依次跪拜。父亲在每尊菩萨前都要磕九个头再行九次合掌礼,我们跪拜时,他就站在旁边祷告神灵保佑我们,轮到我时,父亲的祷告声似乎显得更加虔诚,"菩萨保佑我这老果儿(泰兴方言即最小的孩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长大!(我从小体弱多病,成为父母焦虑的问题孩子)"那份舐犊深情在声声祷告中表露无遗,如山的父爱就在这庄严的仪式中,混杂着烟雾静静地弥散蔓延,至今,那香和蜡烛的味道都让我觉得亲切!
拜完菩萨,父亲重新净手后,再燃上三炷香,爬上梯子。房子二梁上挂着悬空的木架,上面安放着祖宗牌位,父亲把那柱香插在香炉里,下得梯子,跪拜众祖先,磕三个头行三次合掌礼,然后我们依次行礼,而父亲也还是站在旁边,小声祷告祖宗保佑我,他是想求得天地神灵都来保佑他这个小女儿,如此,他才会安心。
从这一刻起一直到大年初一,父亲就端坐在椅子上,一边吟唱他那本纸质极薄的已经发黄的线装书《玉如意》――即现在的折子戏《姐妹易嫁》,一边小心看护着香火,待到香火将燃尽时马上续上,整个除夕夜,他都会让这香火一直燃着……
我们这里的习俗,除祖宗的周年祭日需要祭祀外,一年中还有清明、七月半、冬至、除夕四个公祭日。
从我的爷爷奶奶、太爷太太,上推至四代,所有老祖宗的祭日,父亲都记得特别清楚,每逢祭日,他便拿出锡箔纸,坐在大门口认真细心地折叠着诸如元宝、稞子之类的祭品,我走过他身边时,他便会叫住我耐心地教我折叠……
家里的四方桌子,平常都是沿桌面上的板线东西方向放的,而祭祖时必须沿南北方向放好,放上椅子,摆上筷子,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父亲在桌子前面点燃他折叠好的祭品,吩咐我们不要碰到桌椅,在拜垫上给老祖宗们磕头请安,父亲嘴里则念念有词,请老祖宗保佑我们健康平安……
等饺子的热气散去,父亲小心翼翼地挪挪椅子,意思是老祖宗吃好饭了可以走了。每当这时,屏气凝神的我们才会松一口气。把桌子重新挪回原来的方向,父亲把祭祖的饺子倒进锅里,重新烧沸腾了捞起给自己吃,他说重新烧一下是去掉祖宗留下的气息,小孩子是不能吃的,因为这气息如果伤到小孩子,会让小孩夜卧不安,而他是一家之长,应该当仁不让!
渐渐长大了,开始接触科学与唯物论,对父亲的这套迷信便有些嗤之以鼻,父亲丝毫不理会我的蔑视,依然会把最深情的祷告诉诸我耳边,依然发自内心地去跪拜,他不理会我的无理与无畏,内心里充满信仰,不管如何,这个仪式过后,他内心安然,他的祝福已经求诸祖宗神灵,他相信神明定会灵验,这于他已经足够!
再后来,我做了母亲,进而做了祖母,深深体会到了父亲的这份恩慈。
为了我的儿孙,我也愿意在重要时刻上香进拜,虔诚地跪倒在神明与祖宗面前,许愿祝祷,透过袅袅的香烟,我看到为我伏倒在地满怀敬意膜拜的父亲的身影,那份挚爱亲情就在香烟中四处延展,我知道,那里有亲人至高无上的爱,真的,神明已经灵验了!
父亲已经离开我十三年了,逢年过节以及他的忌日,我只能在心里为他焚香行礼。
对亲人的思念化作了那些无处可去的乡愁,它们频频随梦而入,牵萦缭绕,与之相照的只有天边的那弯月,月缺又月圆,周而复始!
那些渐消渐无的香烟啊,模糊着岁月深处的过往,让梦迷离,情无可往!
无言书香,本名周素香,做过代课教师,如今做着小生意,也学着画些写意花鸟画,在红尘中摸爬滚打着,不忘初心。生活中"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于凡尘间搜集着点点滴滴的爱与感动,与一树花开间,与一段文字间,与一幅写意间,快意人生。愿以诗意舞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