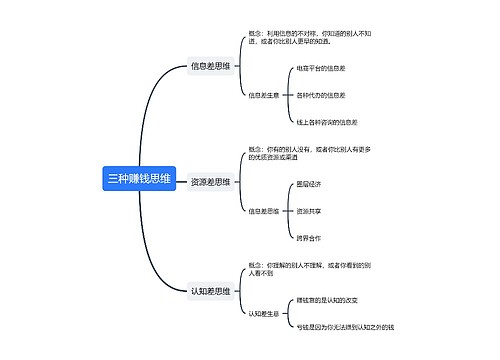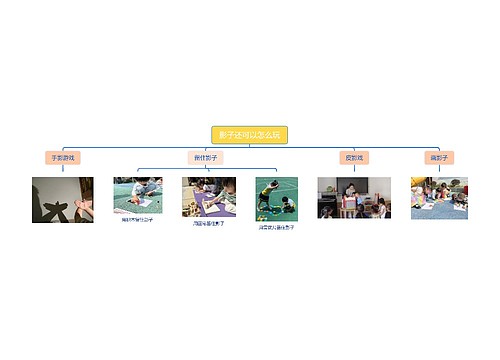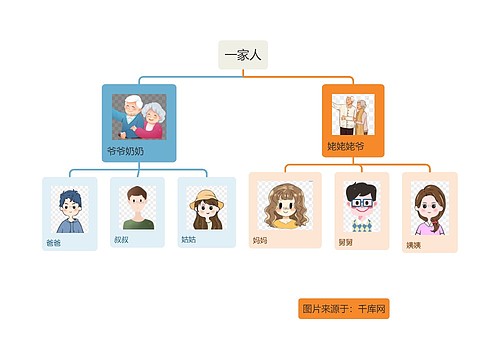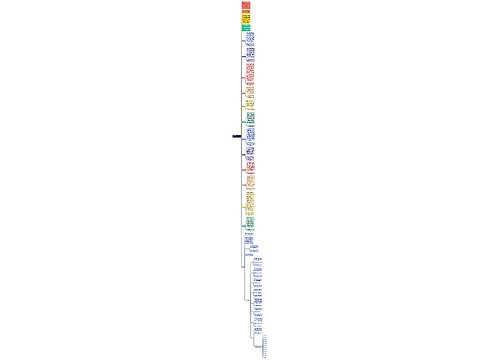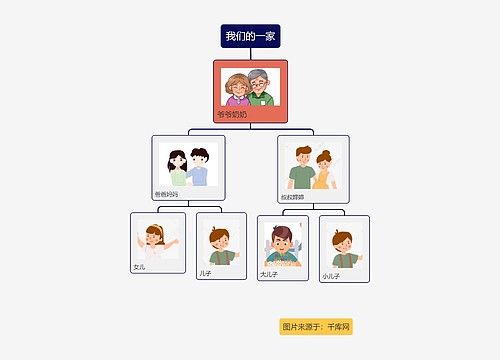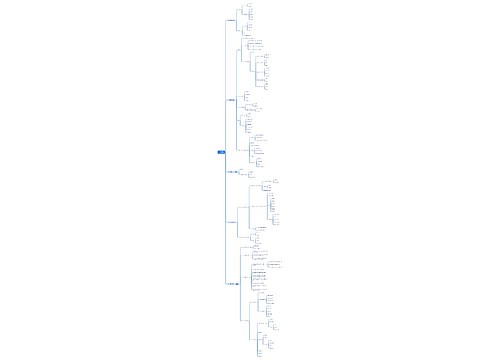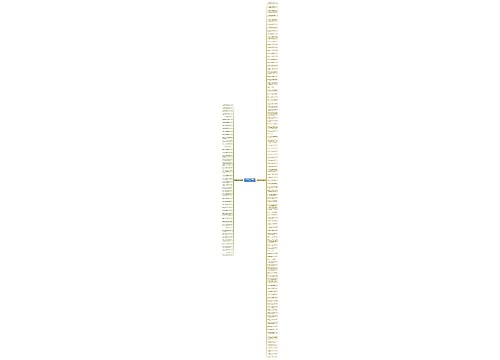中国不受产油国等动向影响,有稳定的能源供应之时,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国内市场扩大后,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就会更深。
时任相关领导这样说道;尽可能多地出口石油,反过来我们才能得到许多好东西。
用石油换回的外汇都换成了各种进口的技术和设备,比如乙烯生产装置、化纤设备和技术、石油开采的钻机、地震仪器等,这些都有利于中国轻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化工工业的发展。
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商界为争取来自中国的石油,积极斡旋,希望促成《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这也让中国在外交上具有了更大的主动性。
当然有些扯远了,我们在这里重点想讲的是中国因为与世界交汇而拥有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然而这都是非常大层面的东西了,细化到我们每个人身边,就是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招工考试这些老办法,或是改革发展到后面,可以更加宽松地离开乡土,进城务工。
更多的厂子开起来了,更多的农村人进城了,原本的城市显得那么狭小,城区的扩大就提上了日程表。
来,回忆我们一开始说到的,城市的土地所有制是国有制的基本情况。同时,稍微对中国发展有信心、有远见的人,敢于发财的机会来临了。这条利益链上的每一个环节:从把土地的总盘子变大,再到让房子拔地而起所需的材料人工,以及各类部门从放贷到审批过关…都是一场饕餮盛宴,都瓜分着宽而深的工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带来的好处。
来,再回忆一下相关领导的话语: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的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那五十年怎么能变呢?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
在让改革进程(城)更加顺滑同时,土地作为城市运作的资产,以更好的城建吸引更多的产业进驻,进一步吸引更多的打工人,让房价更高。不得不让人赞叹:好一出左脚踩右脚上天的把戏。虽然这出戏在很多地方玩砸过,比如当年的海南旧事。
但问题是,用这片广袤的土地吸引外资或是利用本地要素进行工业化、城市化的禀赋并不均一,太史公那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呼号犹言在耳。
那些短暂吹起来的城市如过眼云烟一般化为鬼城:没有人愿意花钱买的资产,我们通常称其为泡沫,泡沫破了,长了双脚会跑路的人也就散了。
但问题是,泡沫的大小也是不一的,行政公器用于"扭曲市场"(这个词的假设就是有个没有扭曲的市场,虽然我们至今没有见到过)的力量也是不一的。决定从发展中切走蛋糕的力量也是不一的。
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那些能够把公器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结合的更好的城市胜出。
毕竟,人力终有穷尽,发一打文件就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只存在于梦里:沿海画的那么多圈,剩下来的赢家也就那几个。
再度复读一个经济学常识:一个人的支出等于另外一个人的收入,从经济发展来说,长期看劳动生产率,短期则看债务。另外,欠的债都是要还的。尽管我们都知道另外一个常识:用的人民币都是央行的债,在真实的经济增长爬坡缓慢的时候,可以靠印钱来增加市场里的流动起来的钱,用发行新债还旧债,用时间长但总收益更高的债吸收的钱来还即将到期的旧账。但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更夸张的两极分化。穷人过了今天没明天,甚至是负储蓄的状态,又怎么有余钱投资,去让财富别缩水呢。
我们还要知道,经济学知识显然只是众多类别知识中的一种:我们毕竟是活在互联网深度改造的国民经济的国度里,如果能够在技术上达到对主要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进行动态监测的同时(比如所谓"一城一策"),及时地配置相关力量,消除可能爆发的不稳定因素,那么高居不下的房价其实可以通过"拖"来完成,俗称"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毕竟人还是适应性很强的一种生物嘛:通勤几个小时,上班几个小时,睡觉几个小时,一天就过去了…然后再周而复始。
话说回来,房地产是不是一个"恶",属于一种价值判断,反对它的人与支持它的人都能找到非常多的理由。所以毫无意义,问题是"你"个人打算怎么办?无论你个人怎么想,在房价往上推高这个环节里,很多人都能因为共同的利益而聚合团结起来,所以聪明的个人明智而市侩的选择是"避其锋芒,选择租房"。
另外城市不相信眼泪,无论这个城市叫不叫莫斯科,租房都无法负担得起的人,只会被各种直接存在的或是间接存在的"机制"踢去该去的地方。
"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内在规律化为外在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资本的增殖是对工人最有利的事情。这一点必须同意。要是资本停滞不动,工业不会停止不动,而是会垮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垮台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作为幽灵的马克思在文字上,或许还在批判着我们生活的时代。
虽然时常高呼躺平,但哪里又真躺的平。为了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落脚之地,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关注南城睡到自然醒的个人空间_哔哩哔哩_Bilibili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