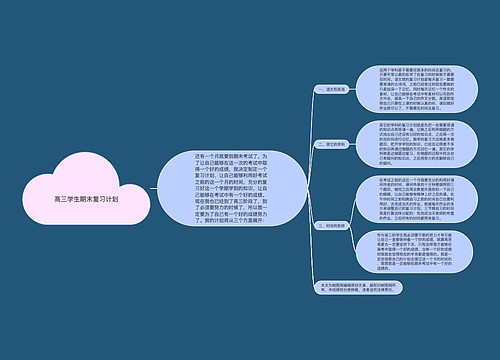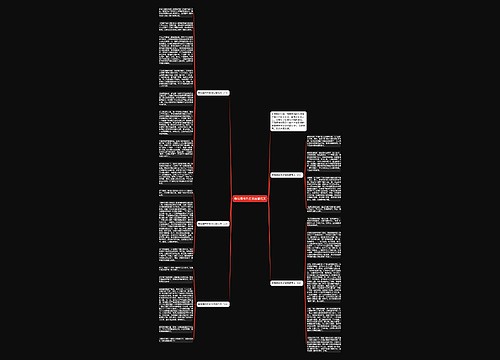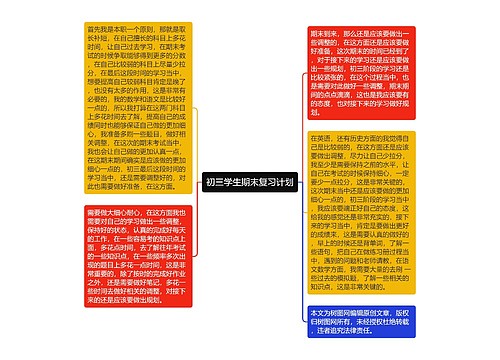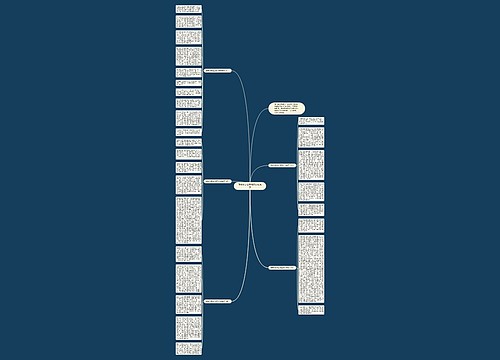高中生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思维导图
千百回
2023-0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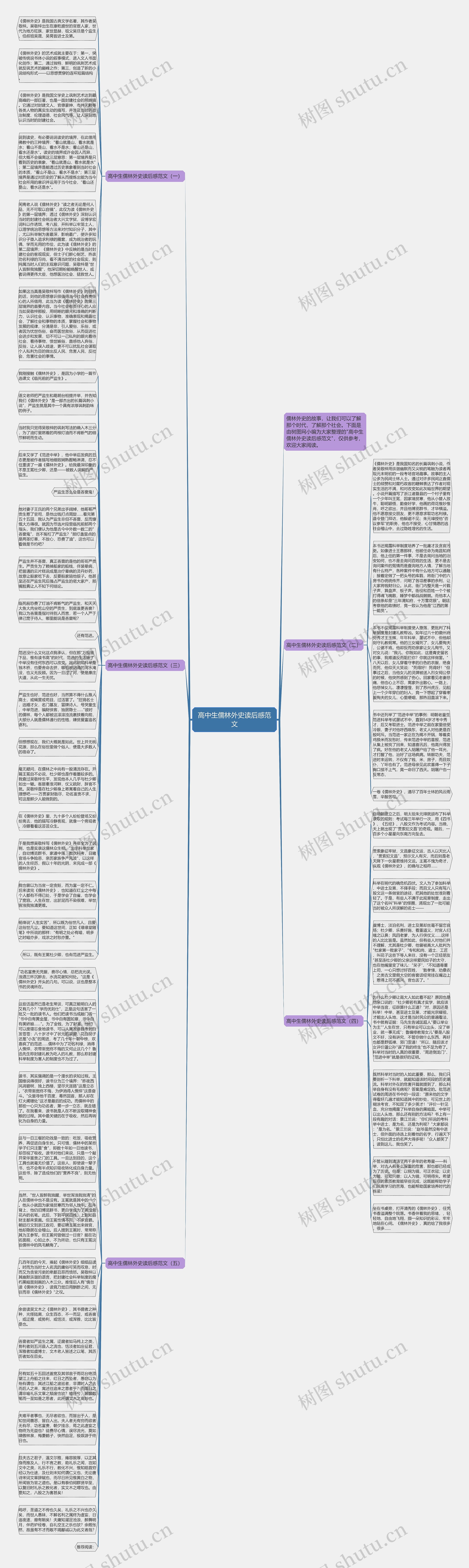
高中生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
中外名著读后感
《高中生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由中外名著读后感网发布,主要内容:儒林外史的故事,让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了解那个社会。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高中生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高中生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c15819f33dd1e2e4eb5cebed050bb80e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高中生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儒林外史的故事,让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了解那个社会。下面是由树图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高中生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高中生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一)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其作者吴敬梓。吴敬梓出生在康乾盛世的官宦人家,世代为地方旺族,家世显赫,祖父吴旦是个监生,伯叔祖吴晟、吴昺皆进士及第。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主要在于:第一,突破传统说书体小说的叙事模式,进入文人书面化创作;第二,通过独特、鲜明的讽刺艺术成就反讽艺术的巅峰之作;第三,创造了新的小说结构形式——以思想贯穿的连环短篇结构。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讽刺艺术达到最高峰的一部巨著,也是一面封建社会的照妖镜。它通过对封建文人、官僚豪绅、市井无赖等各类人物的真实生动的描写,并涉及当时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社会风气等,让人深刻地认识当时的封建社会。
说到读史,有必要说说读史的境界,在此借用佛教中的三种境界:"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读史的境界或许会因人而异,但大概不会偏离这三层意思:第一层境界是只看到历史的表象,"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第二层境界是能透过历史表象看到当时社会的本质,"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层境界是通过对历史的了解从而提炼出能为当今社会所用的意识并运用于当今社会,"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闲斋老人说《儒林外史》"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此仅为读《儒林外史》的第一层境界;透过《儒林外史》深刻认识当时的封建社会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设博学宏词科以作诱饵,考八股、开科举以牢笼士人,以理学统治思想等方法来对付知识分子,其中,尤以科举制为害最深,影响最广,使许多知识分子堕入追求利禄的圈套,成为统治者的玩偶、学而无用的市侩,此为读《儒林外史》的第二层境界;《儒林外史》中反映的是当时封建社会的客观现实,但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看不清当时的社会现实,则纯属当时人们的主观意识问题,吴敬梓是"世人皆醉我独醒",他深切期盼能唤醒世人,或者说得更伟大些,他想医治社会、拯救世人。
如果这当真是吴敬梓写作《儒林外史》的目的的话,则他的思想意识很值得当今社会有责任心的人所借用,此当为读《儒林外史》的第三层境界的首要内容。当今社会有责任心的人应当如吴敬梓那般,用明晰的眼光和准确的判断力,认识社会、认识事物,准确表现和揭露社会,了解社会和事物的本质,掌握社会和事物发展的规律,分清是非,引人爱俗、乐俗,或者因为忧世伤俗,奋而医世救俗,从而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切不可以一己私利的眼光看待社会、看待事物,愤世嫉俗,蛊惑他人弃俗、反俗,让人误入歧途,更不可以扰乱社会谋取个人私利为目的做出反人民、危害人民,反社会、危害社会的事情。
高中生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二)
《儒林外史》是我国知名的长篇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用诙谐幽默而又尖锐的笔触为读者再现元末明初的一段考场官场趣事。故事的主人公多为民间士林人士。通过对许多民间正直儒士的倾赞和对腐朽政客的鞭棘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对改变如此灰暗世界的期望。小说开篇描写了浙江诸暨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少年叫王冕,因家境贫寒,他从小替人放牛,聪明颖悟,勤奋好学,他画的荷花惟妙惟肖,呼之欲出,并且他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他不愿意接交朋友,更不愿意求取功名利禄。县令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朱元璋授他"咨议参军"的职务,他也不接受,心甘情愿的逃往会稽山中,去过隐姓埋名的生活。
本书还揭露科举制度培养了一批庸才及贪官污吏。如像进士王惠那样,他被任命为南昌知府后,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去询问当地的治安如何,也不是去询问百姓的生活,更不是去询问案件的冤情而是查询地方人情,了解当地有什么特产,各种案件中有什么地方可以通融;接着定做了一把头号的库戥,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差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从此,衙门内整天是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散,睡梦中都战战兢兢。而他本人的信条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朝廷考察他的政绩时,竟一致认为他是"江西的第一能员"。
本书不仅揭露科举制度使人堕落,更批判了科举制度是封建礼教帮凶。如年过六十的徽州府穷秀才王玉辉,年年科举,屡试不中,但他却刻守礼教纲常。他的三女婿死了,女儿要殉夫,公婆不肯。他却反而劝亲家让女儿殉节。又对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难道反而阻拦你?你就这样做罢。"八天以后,女儿穿着守孝的白色的衣服,绝食而死,他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但事过之后,当他女儿的灵牌被送入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伤心。回家看见老妻悲痛,他也心上不忍,离家外出散心。一路上,他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到了苏州虎丘,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竟一下想起了穿着孝服殉夫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下来。
书中还列举了"范进中举"的事例:明朝老童生范进科举考试屡试不中,直到54岁才考中秀才,后又考取进士。范进中举之前在家里倍受冷眼,妻子对他呼西唤东,老丈人对他更是百般呵斥。当范进一家正在为揭不开锅,等着卖鸡换米而发愁时,传来范进中举的喜报,范进从集上被找了回来,知道喜讯后,他高兴得发了疯。好在他的老丈人胡屠户给了他一耳光,才打醒了他,治好了这场疯病。转眼功夫,范进时来运转,不仅有了钱、米、房子,而且奴仆、丫环也有了。范进母亲见此欢喜得一下子胸口接不上气,竟一命归了西天。胡屠户也一反常态,
一卷《儒林外史》,道尽了百年士林的风云雨雪,辛酸苦叹。
高中生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三)
我刚接触《儒林外史》,是因为小学的一篇节选课文《临死前的严监生》。
语文老师把严监生和葛朗台相提并举,并告知我们《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严监生就是其中一个具有浓厚讽刺韵味的例子。
当时我只觉得吴敬梓的讽刺写法的确入木三分,为了油灯里燃着的两根灯油而不肯断气的细节鲜明而生动。
后来又学了《范进中举》,他中举后发疯的丑态更是被作者描写地细致娴熟酣畅淋漓,忍不住重读了一遍《儒林外史》。给我最深印象的不是王冕杜少卿,还是——被数人误解的严监生。
严监生怎么会是吝啬鬼!
他对妻子王氏的两个兄弟出手阔绰,他哥哥严贡生惹了官司,是他出钱打点周旋……看完第五十五回,我认为严监生非但不吝啬,反而慷慨大方得很。就因为节选片段里临死前那两个指头,我们便认为他是古今中外数一数二的"吝啬鬼",岂不冤枉了严监生?"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这也可以看做是节约吧?
严监生并不吝啬,真正吝啬的是他的哥哥严贡生。严贡生为了赖掉船家的船钱,佯装晕病,把普通的云片糕说成是治疗晕病的灵丹妙药,故意让船家吃下去,反要船家陪他银子。他甚至还在严监生死后强占严监生的偌大家产,那嘴脸真让人不知下何结论。
临死前恐费了灯油不肯断气的严监生,和天天大鱼大肉坐吃山空的严贡生,到底谁更吝啬?我以为吝啬是指对待别人而言,若一个人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哪里能说是吝啬呢?
还有范进。
范进没什么文化这点我承认,但在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范进的生活除了中举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因此明知科举是独木桥,也要舍命去挤,哪怕被汹涌的河水淹没,也义无反顾。因为一旦过了河,便是康庄大道,从此一生无忧。
严监生也好,范进也好,当然算不得什么雅人高士,或蝇营或苟且,过活罢了。"狂狷名士,逃婚才女,名门基友,冒牌诗人,号哭童生,中举范进,骗财侠客,独居隐士……"彼时的儒林,每个人都被这滚滚浊流裹挟着向前,大部分人就是儒林通行的性格,嫌贫爱富追名逐利。
但想想现在,我们大概就是如此。世上并无桃花源,那么在俗世里做个俗人,便是大多数人的宿命了。
毫无疑问,在儒林之中尚有一股清流存在。开篇王冕自不必说,杜少卿也是作着墨较多的。我查过吴敬梓生平,发现他本人几乎与杜少卿如出一辙。客居秦淮河畔,仗义疏财,辞官不就。吴敬梓是在杜少卿身上寄寓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吧——万贯家财散尽,功名富贵不求,可这是鲜少人能做到的。
在《儒林外史》里,九十多个人纷纷登场又纷纷离去,他的描写冷静客观,就像一个旁观者,冷眼看着这芸芸众生。
于是我想吴敬梓写《儒林外史》并非全为了讽刺,也是实录这儒林众生相。"出生科举世家,自幼博览群书,家道中落,数次科考,目睹官场斗争险恶,亲历家族争产风波",以这样的人生经历,假以十年的光阴,来完成一部《儒林外史》。
我也曾以为当官一定贪赃,而为富一定不仁。后来读完《儒林外史》,也知道在红尘之中每个人都有不得已处,于是学会了自省,也学会了宽容。人生在世,出淤泥而不染很难,举世皆浊我独清更难。
杨绛说"人生实苦",所以既为俗世凡人,且爱这俗世凡尘。要知道这世间,正如《缘缘堂随笔》中所说的那样:"有明之处必有暗,明多之时暗亦多,戏浓之时愁亦重。"
所以,既有王冕杜少卿,也有范进严监生。
高中生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四)
自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就颁布了科举录取的规则: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用《四书》、《五经》、八股文作为考试内容。当晚,天上就出现了"贯索犯文昌"的奇观。随后,一百多个小星星向东南方向坠去。
贯索象征牢狱,文昌象征文运,古人以天比人,"贯索犯文昌",预示文人有灾,而后则是老天降下一伙星君维持文运。王冕不愧为奇才,纵观《儒林外史》,的确与之相符……
科举在明代的确危机四伏。文人为了参加科举、中进士及第,不择手段;而且文人只有写八股文这一条做官的途径,把其他的处世准则看轻了。于是,有些人不满于此规章制度,走出了这个名叫"科举"的怪圈,涌现出了一批可能当时被众人所误解的名士——
虞博士,淡泊名利,进士及第却丝毫不留恋官场;杜少卿,乐善好施,看重道义,对官人们嗤之以鼻;凤四老爹,为人行侠仗义……这样的人比比皆是。虽然如此,但有些人对他们并不理解,尤其是杜少卿,他曾被高大人批判为"杜家第一败家子"、"专和和尚、道士、工匠、叫花子这些下等人来往,没有一个正经朋友"甚至连杜少卿的父亲这样爱民如子的太守,也在他嘴里变了味儿:"呆子"、"不知道尊重上司,一心只想讨好百姓,‘敦孝悌,劝桑农’之类古文里假大空的客套话经常挂在嘴边上,惹得上司不高兴,官也丢了。"
为什么杜少卿让高大人如此看不起?原因也是他亲口说的:"杜少卿若有真才实学,就应该中举当官,征辟算什么正道?"对,原因还是科举!中举,甚至进士及第,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出人头地,这才是当时民众的普遍看法,书中就有证据:马先生告诫匡超人"要以举业为主""人生在世,只有举业可以出头,没了举业,就一事无成";鲁编修教育女儿"要是八股文不好,没有讲究,不管你做什么东西,再好也都是野狐禅、邪门歪道!"所以,随后该才女评价蘧公孙"误了我的终生"也不足为奇了。科举对当时的人真的很重要,"周进倒龙门"、"范进中举"就是很好的证明。
既然科举对当时的人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只要剖析一下科举,就能知道该时间段的历史潮流。科举对外在的危害开篇就提到了,那么科举自身有没有毛病呢?答案是肯定的。批范进试卷的周进在书中的一段话:"原来他的文字得看好几遍才能知道其中的妙处,可见世上的糊涂考官,不知屈了多少英才!"评价一针见血,充分地揭露了科举自身的黑暗面。中举可以出人头地,那么还有别的方法吗?书上有一段有趣的对话:景江兰说:"你们所说的考科举中进士,是为名,还是为利呢?"大家都说:"是为名。"景江兰说:"赵爷虽然没有中进士,但外面的诗选上刻着他的名字,行遍天下,只怕比进士的名声大得多呢!"众人都笑了。读到这儿,我也笑了。
不管从隨到清活了两千多年的老寿星——科举,对古人有多么深重的危害,那也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希望现在的素质教育能早些完成,这既能帮助学子们脱离学习的苦海,也能帮助国家培养时代的栋梁!
坐在书桌旁,打开清秀的《儒林外史》,任凭书香溢满整个院落。书香伴着我的思绪,,轻轻地、自由地飞翔,撷一朵知识的彩云,牢牢地贴在心间。《儒林外史》,真的给了我很多,很多……
高中生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五)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
这些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可真正能明白人的又有几个?"学而优则仕",正是这句话害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他们把读书当成敲门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圆如意,书中自有美娇娘……"。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垂髫考到白发苍苍: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鲁迅先生称封建礼教为吃人的礼教,那么称封建科举制度为害人的制度也不为过了。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王国维说得很好,读书分为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立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奋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才是最后的成功。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
这与一日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自身力量。这些书,除了造成他们的"营养不良",别无他用。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
余尝读吴文木之《儒林外史》,其书儒者之种种,光怪陆离,众生百态,不一而足,或吝啬,或迂腐,或势利,或恬淡,或浑雅,比比皆是也。
吝啬者如严监生之属,迂腐者如马纯上之类,势利者则五河县人之流也,恬淡者如庄征君,浑雅者如虞博士,文木老人皆述之以笔,其历历者如在目矣。
另有如五十五回述盖宽及其邻翁于雨花台绝顶望江上舟船之往来,红日之西坠者,愚窃以为殆有谓也:其述江船之逡巡者,非谓时人之去而后人之来,寓述往追来之意者乎?而落日之谓非喻礼乐文章之颓废也欤?噫吁兮,聊聊数笔而一至如是之思者,此所谓文木之高妙也。
夫难平者事也,无尽者欲也,而皆出于人,是知世间善恶,皆自人出。夫人者无有穷而欲者无有尽,功名富贵,朝夕挂念,焉之此虚妄之物终为无益也?徒费尽心情,误尽流光,莫如啸傲林泉,梅妻鹤子,快然自足,极娱游于终日也。
且夫古之君子,温文尔雅,雍容敦厚,以正其身而推及人,行不言之教,助礼乐之闻,岂如文中之类,礼乐不行,教化不兴,惟知皓首穷经以为仕途,及仕则未知何谓仁义也,无论唐诗宋词文章辞赋也,而尽日所见惟黄白之物,所闻皆为官之道也。是以有泰伯祠群贤毕至,以复旧时礼乐之教化者,实文木之喟叹也。由是知之,八股之为害甚矣!
呜呼,圣道之不传也久矣,礼乐之不兴也亦久矣,而世人愚昧,不解名利之属终为虚妄,日追夜逐,靡有朝矣!夫庸知濯足沧浪,醉舞明月,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之乐也欤?余既怅然,故虽有不才而敢不竭鄙诚以为此文者哉?
推荐阅读:
查看更多
阅读《学习型管理》一书读后感思维导图
 U478228048
U478228048树图思维导图提供《阅读《学习型管理》一书读后感》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阅读《学习型管理》一书读后感》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a8ecfaff84a00177a72b5365381785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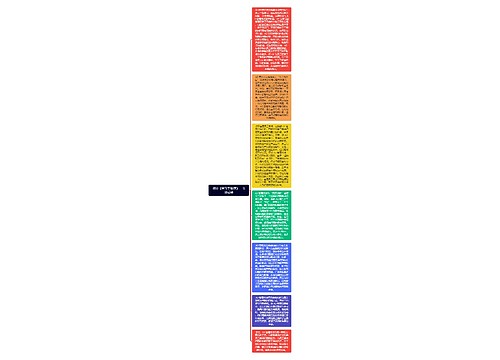
高中生物调节机制对比思维导图
 U676922552
U676922552树图思维导图提供《高中生物调节机制对比》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高中生物调节机制对比》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1e2bf1adb5e6526a1eb26d16ef7479e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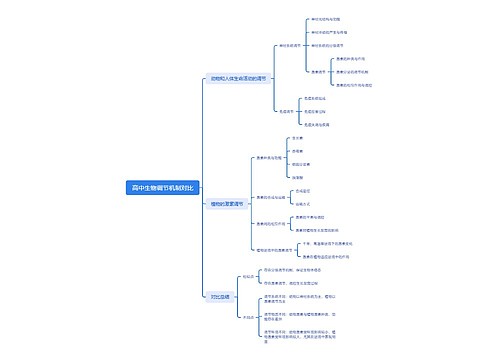
相似思维导图模版
首页
我的文件
我的团队
个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