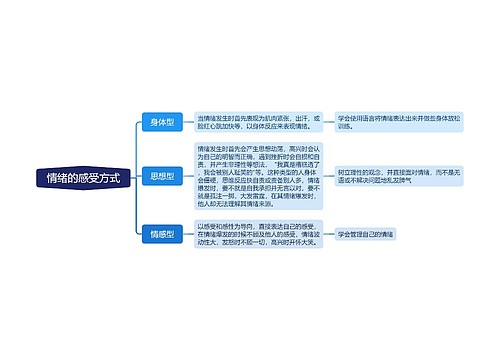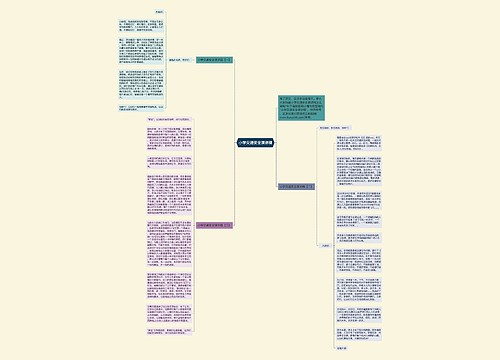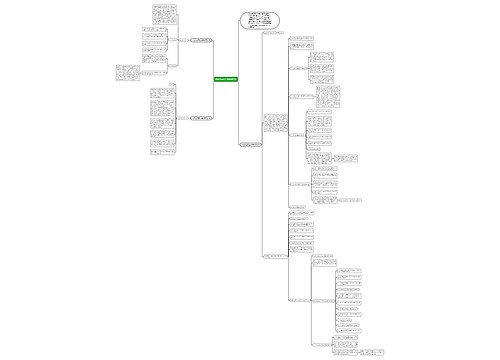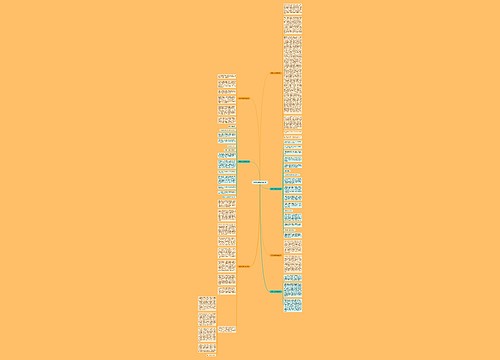史铁生推着轮椅缓缓地进了园子。他想寻找生的理由,或者死的解脱。一个返乡的知青、一个失业的大龄青年,一个多愁善感的大脑,再加上一个高位截肢不得不依靠透析机活着的现实,史铁生的命运真是多舛!母亲悄悄地跟进了园子,落日的余辉把她慌慌张张的影子拉得悠长,满脸的焦灼终于在看到儿子的一刹那散去。她就这么怔怔地盯着儿子倔强的背影,又怕他蓦地转身发现自己,便远远地守着、藏着。地坛的风翻动着安详的落叶,轮椅的车轮轧过青青草坪,母亲瘦削的脚印散落在地坛的角角落落。一位焦急的母亲,一个雕塑般的儿子,共同凝成了一个千年的守望。一天又一天,十五年的日子就这样看似平静地过去了。这便是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描述的一幅令人难以释怀的景象。
所有的无奈和悲怆都源自一个现实:儿子在二十岁这个"最狂妄"的年纪突然截瘫了。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和事业的人,却先迎来了残疾。天塌了!他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当时的史铁生想到了死。殊不知,儿子所有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是要加倍的,"她是怎样的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一个痛苦、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面对着一天天长大、却更加孤僻内向的儿子,已经身患绝症的母亲不知度过了多少个空落的白天和不眠的黑夜。只是这一切,儿子在母亲去世后才逐渐体会。
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总是神情肃穆,喉咙里有个莫名的东西在来回嘀咕,胸口憋闷之极,眼泪就潸然而下,父亲的样子便清晰地浮在眼前。八年前的冬天,父亲在我"最狂妄的年纪"上猝然离世。那时,二十三岁的我刚刚走出村子独自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花花绿绿的高楼大厦在带给我新奇的同时,也挑动起了一颗早不安分的心,我精力旺盛,骑着一把破旧而快乐的单车把梦想洒遍整个城市。然而,几乎一夜之间,父亲没了,就像一座山的底座突然下沉,我心底某个巨大的东西被猛然抽走了。我不忍回忆2001年除夕那天那一刻,那一刻父亲想对我说的很多很多,但是病魔已经不容许他多说一个字。他把自己56年人生的最后一瞥留给了母亲、姐姐和我。之后,他的瞳孔便逐渐放空,一双饱经沧桑的泪眼挣扎着,却终于不听使唤地闭上了,永远地闭上了。父亲的灵魂在那一年、那一天最隆重的时刻升起、飘走,留下了全家无尽的遗憾、对未来的恐惧和对他永远的不舍。
那些年,我因过去猖狂而生的深深自责和子欲侍而亲不待所带来的无边痛悔,几乎带走了我所有的眼泪和对未来的希望。每天下午,我总是摇摇晃晃地骑车到二环边上,找个没人的角落,坐着、站着,又坐下…… 这个世界熙熙攘攘,却没有了我的父亲!在辗转反侧的深夜、在若有所失的傍晚,父亲那白发苍苍的脸庞总是似有若无地出现,然后淡去,终于无形。史铁生写到:"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呀,迷迷糊糊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了。’"难道我的父亲也是由于受苦太多被上帝召回?他像天下所有伟大的父母一样,有着低调的自信,坚忍的意志和对儿女毫不张扬的爱。在乡下干了一辈子民办教师的他,自幼丧父,节衣缩食,养家糊口,数十年风雨交加,有几次濒临饿死的边缘。如果上帝赋予众生均等的苦难,我想他早就应该苦尽甘来、颐养天年了。他勤劳善良一生,却不想会以这样一个残酷的方式来结束人世的苦难。
为了父亲,我发誓要活出个人样来。这种念头从八年前出现到现在依然清晰可见。诚如史铁生所言,"儿子想使母亲骄傲,这心情毕竟太真实了"。我开始全面审视自己的过去和将来,对自己的不满与日俱增,逐渐进入一个狂躁奋斗的时期。我不知道以怎样的方式来"使父亲骄傲",只是频繁地更换专业、不止一次地谋划变动工作。我无法确定现在自己慌慌张张所撞开的这条路是不是父亲所希望我走的那条路?那条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是衣锦还乡的荣贵,还是家财万贯的显赫,抑或是内心的豁达、坚强以及与人为善的真诚?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也可以让一切回归本真。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在母亲去世多年之后,终于明白:"我用纸笔在报刊上所撞开的那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盘点自己的人生经历,突然发现,自己八年来的奋斗,在"使父亲骄傲"这个外衣的包裹之下,并没有完全剔除那些世俗功名的念想。唯一能够让父亲欣慰的,就是自己在生活面前所一直具有的积极姿态,和逐渐形成的坚韧、宽厚、真诚和豁达。读完书,我掩卷长思,我想那些所谓的名、所谓的利,就像地坛上空那鸽子的哨声、冗长的蝉歌和空旷的啄木鸟声一样,早就应该在时光的流淌中一起逝去了……
于是,我再一次想到了地坛。地坛的风轻轻拂过四季,轮椅上倔强羞涩的少年在内心的安宁中变得坚强无比;一位失去了父亲的儿子在悲愤的奔波中逐渐长大。古殿檐头的风铃摇个不停,可是那些受尽苦难、大爱无疆的父亲母亲们却永远地走了……
![[收藏]我与地坛读后感受(精选5篇) [收藏]我与地坛读后感受(精选5篇)](https://pic.shutu.cn/shutu/static/2023/04/26/32ae33/32ae33e5f24c286d69ed53c9b063e970.jpeg!w2560?v=41541852)
 U249128194
U24912819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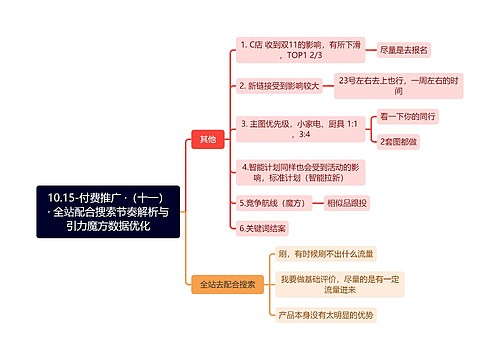
 U382064030
U382064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