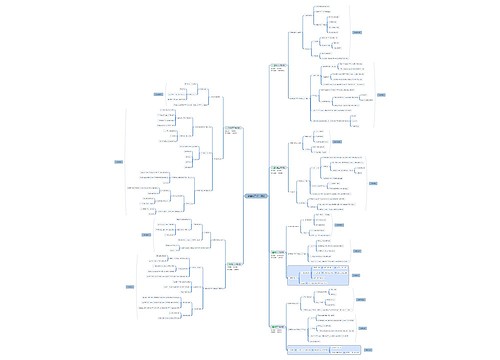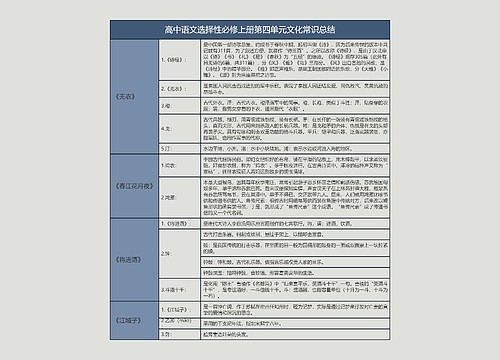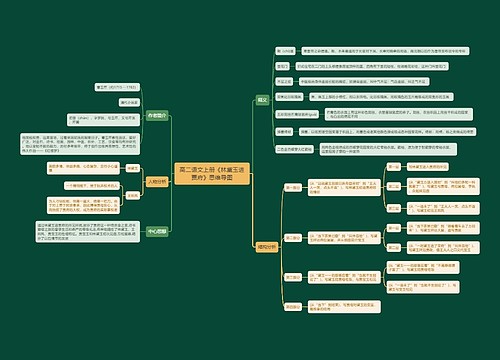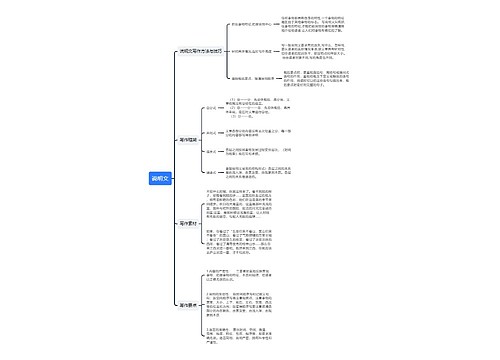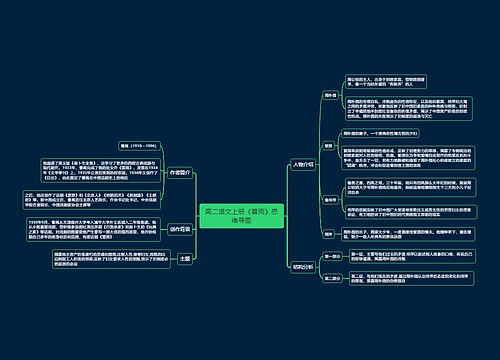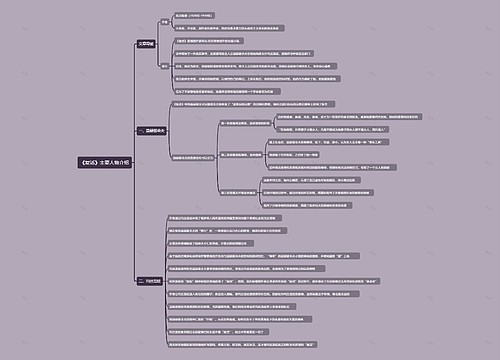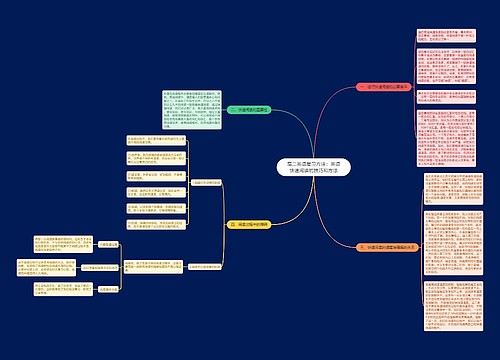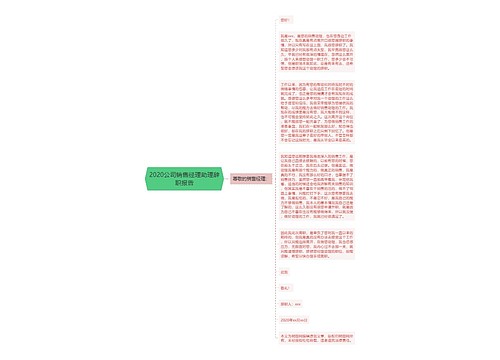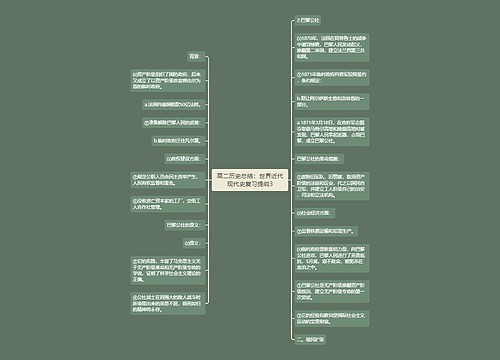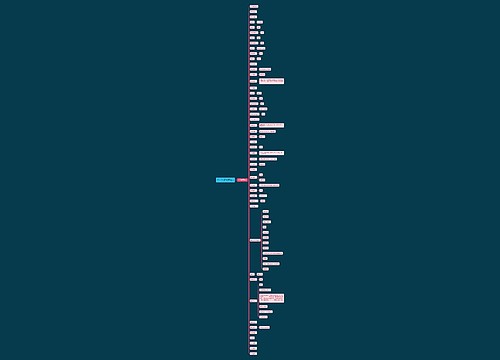离开老街不过五六年光景,还没有久远到可以慨叹物是人非。
事实上,讲离开也未免太不妥帖,就只是不日日归去,仅在长假才停留小憩而已。
老街并未有所进益,阳光天天照进窄窄的弄堂,依旧铺不进谁家厅堂。独门独户的古老设计,让老街人仍旧各过各的日子。
我的老街坊们,怕是有些自私的,至少也是乏些远见的。前些年,拆迁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街坊们虽自称"街上人",但终究是没见过大钱的乡人,憋着劲想发这一笔横财。为能多算些面积,各自动工,在自家门前砌起些不中用的石阶,挤得老街日渐孱弱,也终于坑害了自己。许多日子过得挺滋润的老街坊都得意洋洋得买回了小轿车,但瘦骨嶙峋的老街却再容不进它们,于是街坊们的得意被老街斜眼阻隔在外。于是,一切的趾高气昂狼狈得可笑又不堪。
街坊们在日薄西山时将小车稳稳当当得停在马路边,而后下了车风尘仆仆往家赶。在拐进老街的最后一个转角,必定把步履调得稳重而高傲。车钥匙是绝不能放在兜里,一定要玩得漫不经心,但必要人人都瞧得真真的。我的街坊们是没有精神生活的,因而这一辆小车堆积出一户人家满门的骄傲。
我的街坊们,似乎没有一个经得起时光的打磨。不知什么缘故,乡人总比城里人更易接受时光镌刻的美痕。皱纹也未必有多纵横,要被也未必有多佝偻,但就是有一副雕满时光的精气神。
老街依旧是我的归宿,但我的心与老街却日渐疏离。于是印象中的街坊们就只有两种:面目可亲,或是面目可憎。
记忆最深切的,是住在我对面的一女人,长得并不称得上漂亮,但有极美的双眼皮。她的泼辣爽利像极了王熙凤,但我时常想着想着她,便想起陈小艺,越发觉得相像,倒是这两人重叠在一起。 女孩幼时大约都会寻一个梦的指引,她便是我一直想成为的人:貌不惊人,却不至平淡无奇。去活成一个有韵味的人。
我晓得她终究是凡人,因而并未对她怀有多少艳冠群芳或是驻颜有术的期望,但是我想啊,等到垂垂老矣,韵味历久弥新,那也算得有姿态的人生了。
前年她儿子从单位顺了些钢材,作案的一伙人在案发时早不顾先前吃香喝辣时的兄弟情谊,各自奔波央人摘清关系。可怜的老街上人哪来这许多人脉!她儿子几乎担了全部罪责锒铛入狱,那之后便不常见她了。
"进监牢"在老街上可谓闻所未闻,各怀心事的老街坊顶是嘴不饶人,她便再没脸见人,日日在家以泪洗面了。
偶尔再见到她,总是没一点点神采。嘴角下拉到奇怪的弧度,原先美极的双眼皮也不甚清晰。她总躬身做着活计,叫我疑心她的腰背是再挺不起来的。她懒懒的,或者讲是了无生趣。我仍习惯迎上去唤她,她抬头倒快,极力想伪装出当年的热情,费力扯着嘴角,张口答应,声线嘶哑得我忧心她字子泣血。
我是最见不得旁人狼狈的,于是再见到她也就低头急急走过。倒不知我的好心是否伤害了她,只见得她的生活日日枯萎。我已然不忍再回想她的当年。
她终于还是捱到了些许柳暗花明。她儿子出狱、成家都在我的记忆中略去,就只知现而今,她的小孙儿已亟待出世。她把不堪的日子过得还算红火,现在见人,总和和气气得笑,只是更添了几分讨好,似乎日子能好得这么牵强,是该多惜福,该感谢天命,感谢周遭的一切。
都说同人不同命。崎岖的尽头却不仅是这样苟且的偷安。狭窄的老街倒还挤出条狭隘的出路——读书。街坊中有家里孩子读书出息的,不免多生出些骄矜来,甚而能在老街上肆意横行,仿佛老街是不配容下他们的身影。
她家的小院没有院墙,横了一条长凳,孤零零的。她时常一个人坐在一头,招呼那些骄矜的街坊来坐,赚着笑意开口:"你家姑娘出息....."讲着讲着,便抹起泪来,"不像我家小子,我出心出力,那小冤家无情无义......"都是街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瞧着她这样,不免宽慰几句,只是她日复一日翻来覆去总念叨一样的话语,日子久了,赚足了邻里嫌恶。然后又只剩她一人。长凳又空落落的,不甚安稳。我仿佛亲见了祥林嫂的悲剧。她见了人仍是笑,不带情绪,或许,她终会把太平粉饰到恰恰好?
老街在日复一日的踩踏和修建中愈发崎岖不平,伤害的加深却为因此酌加一点点怜悯。我的街访,着上日渐华丽的外衣在年轮里打滚。他们欣然接受,他们乐此不疲,才得以酌出这心凉的图腾。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121265
U582121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