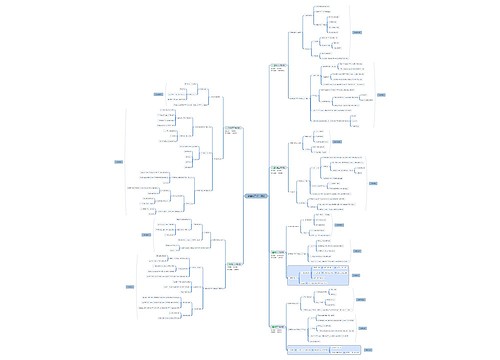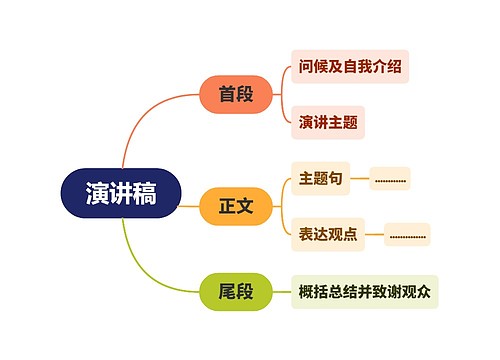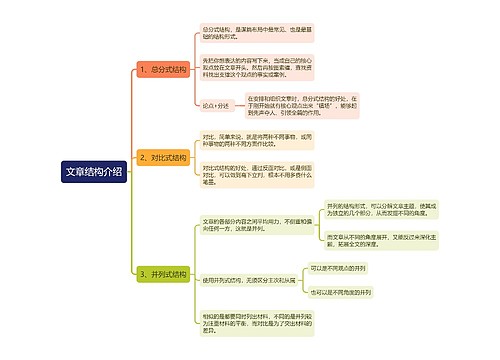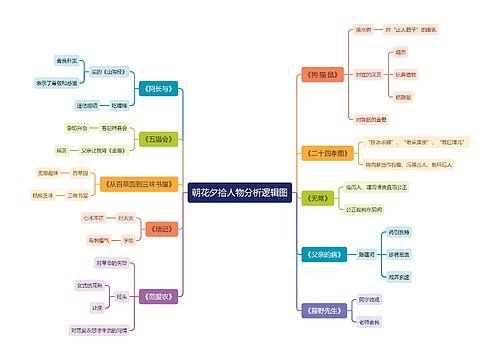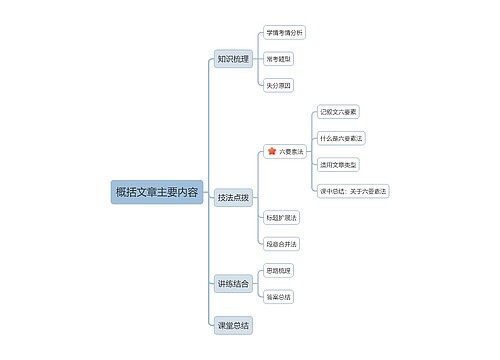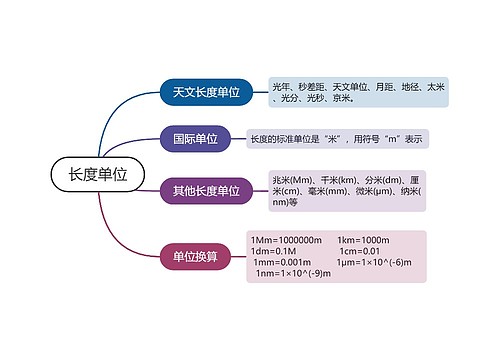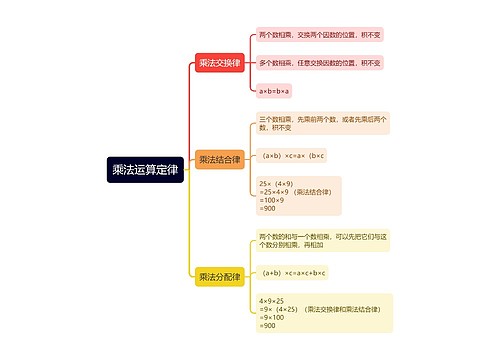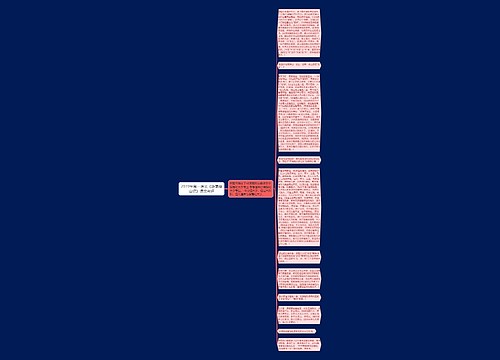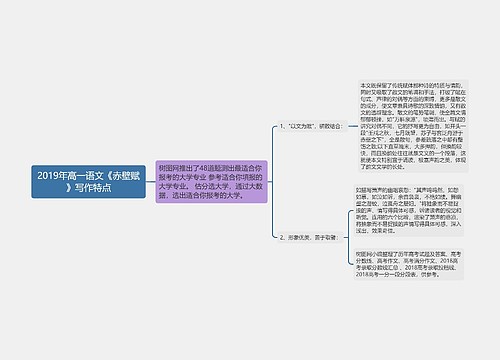2019年高一语文《游褒禅山记》语言特色思维导图
待我归兮
2023-04-19

2019高考进行备考阶段,树图网小编整理了2019高一语文必备知识点,供同学们参考。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2019年高一语文《游褒禅山记》语言特色》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2019年高一语文《游褒禅山记》语言特色》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38dae4eba7b1397d1922ee430299b46c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思维导图
 U633687664
U633687664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10b9a8a2dd2fb4593f8130ef16c320fc

销售经理半年规划思维导图
 U582121265
U582121265树图思维导图提供《销售经理半年规划》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销售经理半年规划》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e614d6bcf03e9318109240a18697c5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