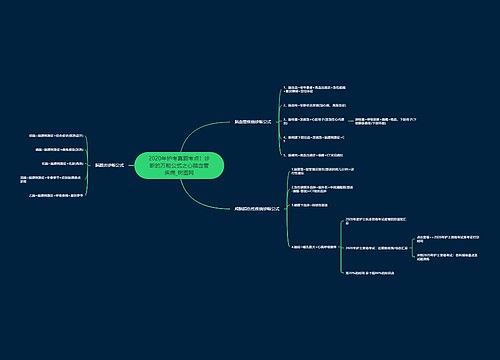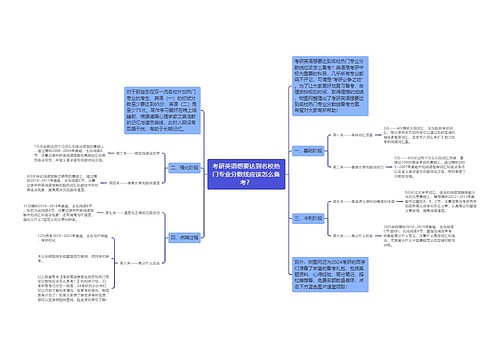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证据规则则是诉讼程序的核心。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因证据规则粗疏而造成实务上错案频出、理论上饱受诟病的双重困局。最近,以解决赵作海冤案为契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在中央统一部署下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简称“两个《规定》”),以规范刑事诉讼有关证据方面的程序,防止刑讯逼供以及其他违法取证行为,避免重大冤案错案的发生。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2001年、2002年颁布《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相比,刑事诉讼程序的这两个《规定》的出台,可谓是“十年磨一剑”,其艰难程度可见一斑。
进而言之,此次两个《规定》的颁布,可以视为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延续以及将要进行的再修改的前奏。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控机关过于强大,被追诉方力量过于弱小,诉讼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理论界已经有了足够清醒的认识。于是,在被追诉方诉讼权利保障方面,增设了侦查阶段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有关内容。
然而,十余年来的司法实践证明,仅仅赋予有限的律师帮助权,难以防止侦查机关刑讯逼供以及暴力取证等违法行为,反而在“命案必破”等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式执法形势下,制造出不少令人震惊的冤假错案。反思之余,理论界与实务界均认识到,刑事诉讼法缺少对证据规则的详尽规定,缺少对程序性违法行为,尤其是违法取证行为的程序性制裁程序,即所谓的“审判中的审判”,是非法取证痼疾难以根除的关键所在。由此,对症下药,两个《规定》的出台,对各种取证行为均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规定,在强调实物证据的同时,突出着力于防范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方面,并初步解决了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程序性制裁问题,从而得到理论界的一致称道。
然而,如果对此抱有过高期望,恐怕恰恰会看到令人失望的结果。众所周知,与民事、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主要是保障法院公正裁判纠纷不同,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还承载着平衡发现事实与保障人权的重要功能。结合当代中国司法实践来看,几乎所有重大冤假错案无不与侦查机关过于依赖言词证据定案,严重侵犯人权,采取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有关。
尽管在具体的取证程序方面更加完善以及在增设程序性裁判程序方面有所建树,然而,在笔者看来,由于两个《规定》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加强程序性制裁而非程序性制约,从而在审判前程序,尤其是侦查程序中,权力控制和互相制约的基本要素缺失,导致国家机关单方治罪的的总体面相没有任何实质性改观。申言之,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得最为充分:
第一,示范性有余,规范性不足。两个《规定》均对侦查机关如何进行讯(询)问以及制作笔录的要求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对于侦查机关依法收集言词证据具有指导意义和示范意义,在执法水平落后地区则更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指出,这些详细的规定,多系以侦查机关的角度出发,为有效追诉犯罪而设立,并不足以规范并防止侦查机关为获取“有利于”侦破案件的供(陈)述而采取刑讯及其他暴力手段,侦查机关仍然可以采取事后补救的方法以掩盖此前的非法取证行为。
第二,制裁性有余,制约性不足。两个《规定》均规定,对于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供述和采取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言,均视为非法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从而确立了对于非法言词证据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尽管如此,由于仍需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以及举证能力上的不足,被告人一方要证明存在违法举证事实必定是难上加难。由于被讯(询)问人对侦查机关的讯(询)问缺乏必要的制约和抗衡,难以防范侦查机关在利益驱动之下实施刑讯逼供及暴力取证行为。两个《规定》将防止非法取证的重心放在审判程序中进行纠错,强调事后制裁,而对侦查程序中的制约手段不置一词,在程序设置方面存在“跑偏”缺陷,在防止违法办案方面必然难奏其效。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笔者不惮直言,对于防止非法取证以及加强对被追诉方人权保障而言,此次两个《规定》的颁布,由于仅仅侧重于程序性制裁而在程序性制约方面无所作为,难免重走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老路。在笔者看来,防止非法取证,保障相对人基本人权,不仅仅是个证据规则范畴的问题,而是与诉讼的基本理念和诉讼结构等基本原理范畴息息相关。只有在这些基本立场得以明确,相关制度才能建立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具体而言,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达成共识:
首先,应该明确确立追诉犯罪与保障人权同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目的。如果保障人权未上升为法律的基本目的,则相应的保障制度难以建立。在此方面,“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明确写入宪法,作为有宪法的“执行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应当将此列为基本目的和任务。同时,我国已经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障人权也即将成为我国的国际义务,在刑事诉讼法中有所体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次,应当切实改革当前的诉讼结构,提升被追诉方的诉讼主体地位。我国长期实行的侦、控、审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结构,属于典型的单方治罪程序,被视为“线性结构”、“流水线型模式”或者“强职权主义模式”,因其缺乏诉讼所必备的控、辩、审三方构造的基本属性,导致刑事诉讼程序制约侦控权、保障人权的功能严重不足而饱受批评。在当前的诉讼结构下,被追诉方被当作诉讼客体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不确立并保障被追诉方的诉讼主体地位,其对诉讼的主动参与程度将严重不足,从而无法制约追诉机关的违法行为。在理论界多数学者看来,废除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是确立犯罪嫌疑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前提;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限度的沉默权,则是保障其诉讼主体地位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这些主张符合刑事诉讼发展规律,符合刑事诉讼基本原理,切中当前刑事诉讼程序问题之要害,应当予以采纳。
第三,应当将律师辩护前伸至侦查程序,保障诉讼程序合法进行。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下,侦查阶段律师只是提供法律帮助,不具有辩护职责和功能。尽管实践反复证明,刑讯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多与律师辩护意见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有关,然而,律师辩护在刑事诉讼中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侵害被追诉人获得律师辩护权利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相反,实践表明,越是疑难重大的案件,律师介入的难度就越大,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被侵害的可能性就越难以遏制。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均应当允许辩护律师在场,不仅可以杜绝刑讯逼供,也有利于促进侦查机关不得不逐步放弃依赖口供定案的基本立场,转而寻求其他侦查取证方式,从而提高侦查水平,实现追诉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如果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对此不做相应改变,两个《规定》对于完善讯问程序所作的努力可能将付诸东流。
正如死刑的存废之争所揭示,再酷烈的刑罚,也难以阻止有人不惜不惧以身试法。套用那句老话,“一切皆要防患于未然”,对于刑讯,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只要设置事后程序性制裁,就能达到遏制其发生的效果。人类的智识已经证明,为防止权力不被滥用,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制约,要优于对权力的滥用进行制裁。在刑事诉讼中,只有当有效的制约程序在前,完备的制裁程序断后,方能编织出一张完整的遏制刑讯的“法网”。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