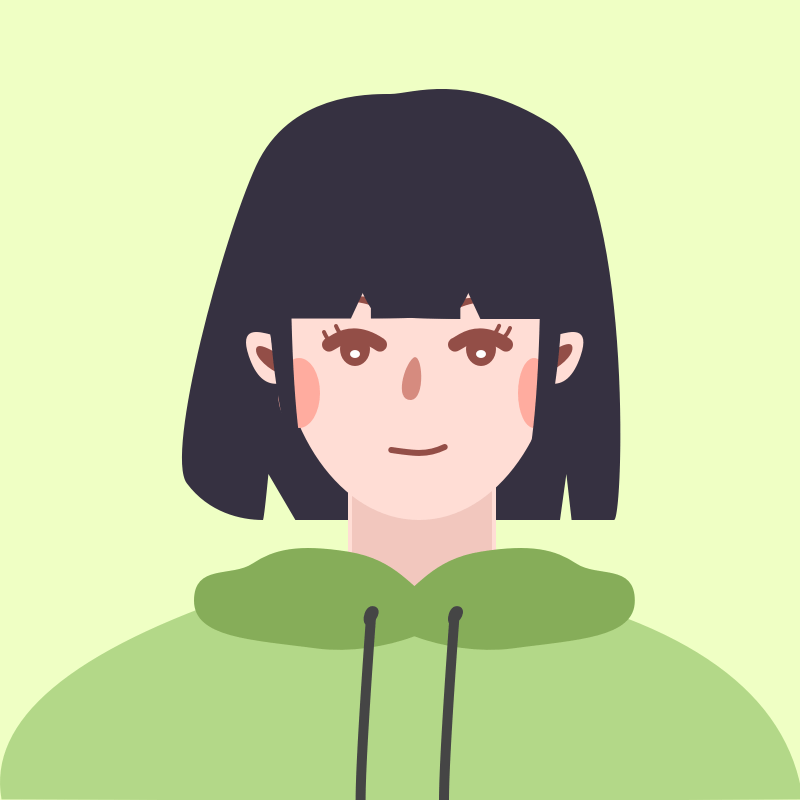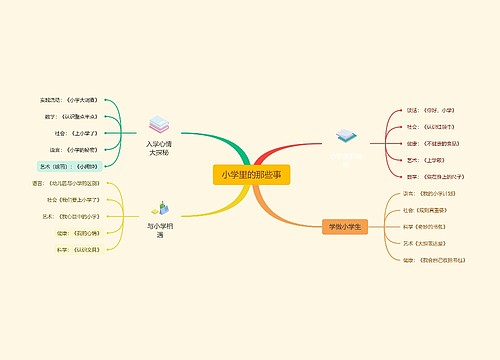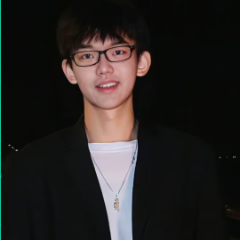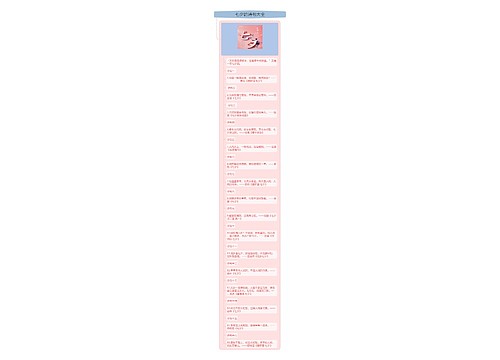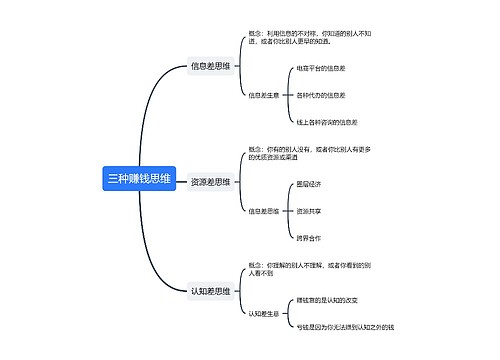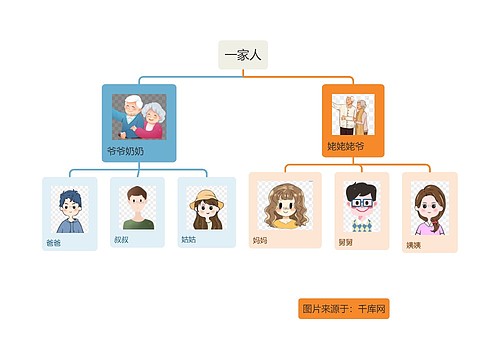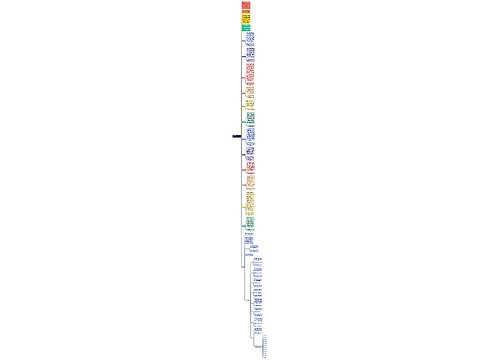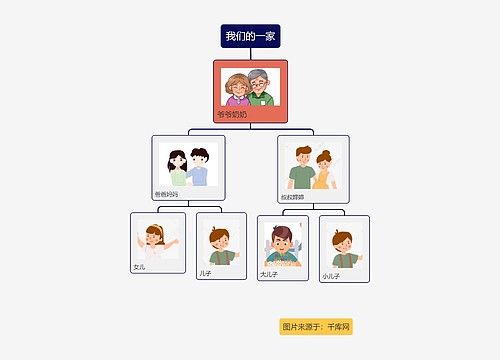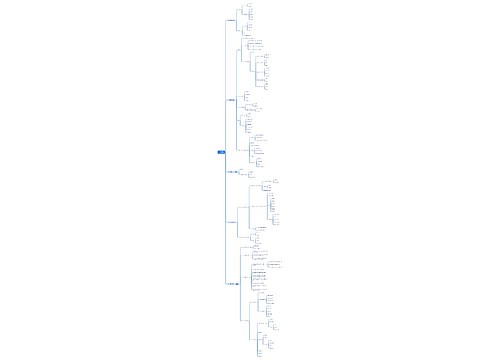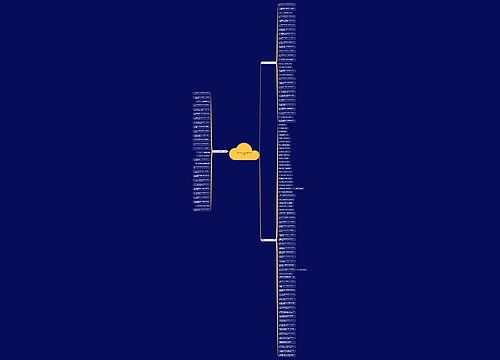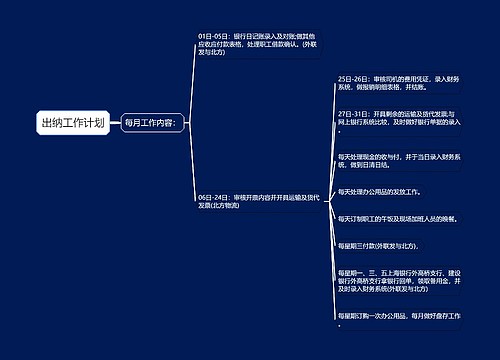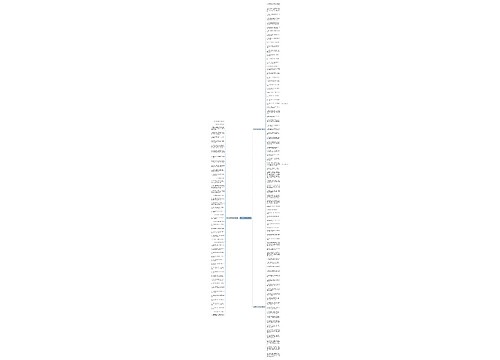一个什么也不做的黄昏和傍晚黄昏的惬意心情说说,不冷不热的气温里黄昏的惬意心情说说,家中安坐。伴着窗外的晚霞在麦田上的光芒渐趋暗淡,只剩下夕阳在西山后面的辉光;辉光映入眼帘,眼睛里满是暮春谷雨时节的沉醉。山前大地华北平原开始之处,这个季节里在干旱的土地之上罕见地弥漫这一种因为大面积种植麦子而来的清凉的湿润气息,在黄昏里这种白天白雾霾里的阳光压抑着在麦子周围很小范围内的气息突然获得了释放,周天彻底的弥漫开来,给呼吸到它们的人带来眼前的欣喜,也带来深远的沉静。
有限时间和空间的人生境遇经常不在我们自己的掌控之中,即便努力向着四面八方尽可能地多走多看,每个人的所见与所感也总是都在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范畴内;这个范畴内充满了既定的路数和重复的冗余,同时还有大量的空白,大量更美好的东西没有来得及进入自己的观感。阅读和书写既是弥补,也是表达,是弥补与表达综合之后在想象的意义上对人生审美际遇的边界拓展。它只在长久的意义上无往而不胜,从来不在眼前直接兑现,但并不妨碍你在当下意识到进入了想象之境的惬意。
没有书写,只自由地阅读,靠在面向夕阳的椅子里,双脚放在前面的凳子上。这放松的自由的时间段落,是一天里的人生丰富性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一天一天的时间安排不可太满,一定要有这样空闲的、发呆的闲逸时光。这其实很不容易,需要警醒自己从俗务中抽身,更需要有窗外的大自然、不被过度打扰的大自然的必要条件。过度聚集的人口与喧嚷的压力日增,地球环境大变,眼前依然有绿色已属不易。
开着台式收音机,同时还开着手机上的收音机,两个台,两个声音,一个在说话,一个在放音乐;电脑也开着,写了一会儿字,转到阳台上的圈椅里仰坐着看六七十年代台湾作者写本地风景的《台湾游记选》,一字一句格外能看得进去,那些后来耳熟能详的宝岛山川在较早的旅行者的眼里,也有未被过分开发的无尽之妙。从那隔海的远方思绪里收回来,但见落地窗外碧绿的麦田和麦田尽头的远山,都正在夕阳里逐渐暗淡下去。
晨昏转换之际,总是自然昭示最明显的时候。这时候人不论在干什么,都应该抬头看看天,看看自己置身其间的这个世界。这在工业社会之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自然而然,全家在院子里吃饭、底层建筑中临窗没有其他建筑遮挡的视野景象之中,这是不必故意也会有的题内之义;工业化城市化房地产化之后,这逐渐变成了一种奢望,一种被密集的人造物遮挡住了朝阳和暮色之后的无可奈何。
建筑过度密集、人口过度集中之后的这种不经意的丧失,加上由之产生的其他与之相应的社会性因素,会使更容易使人陷于焦虑和抑郁,会有莫名的不适和生无可恋似的厌烦。越来越少体会到生命在天地之间的悠然与畅意的结果,其实就是卡夫卡所描绘的地道里的甲虫式的生活状态。这样的状态从开始的被迫接受到后来的不以为意,慢慢就成了现代人的天经地义,就成了他们改变不了甚至也不再想改变的无知无觉的格式。
比如这个黄昏,以这样懒散的、不干什么的方式度过。这样的方式使人非常享受,头脑里漂浮着一些任意的思绪,和阅读有关、和音乐有关、收音机里絮絮叨叨的话语有关,它们幻化组合,逐渐形成一个两个有意味的点。这有意味的点可能是一个词、一句话或者一个意象,其中有的终将生发成一段段文字,形成一段有长度的书写的开端。
这样的时间里,不仅身体放松心态和平,而且思想自由,可以尽情驰骋,类似一种白日梦状态。更多的思绪和线索往往在这样的自由里发芽。
在时间从来都是以分秒计算的从不浪费的日常安排里抽出这样一段时光,享受闲暇的快乐,实在是一种必要的休息也是一种重新启动的准备,此外它的的确确还是一种不假外求的享受,是人生中一种非常舒适的段落,让人觉到生命的可资悠长。多少年后我们回顾人生,也许正是这样一些无事的段落,这样与天地日月同在的片段,一定是组成曾经的美好的重要组成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