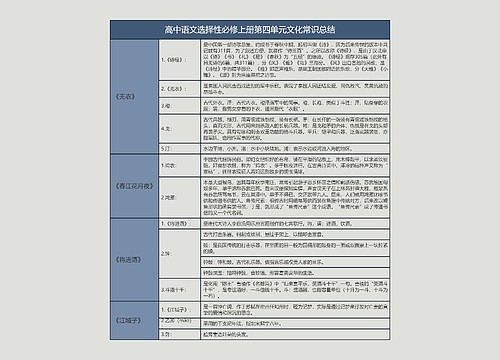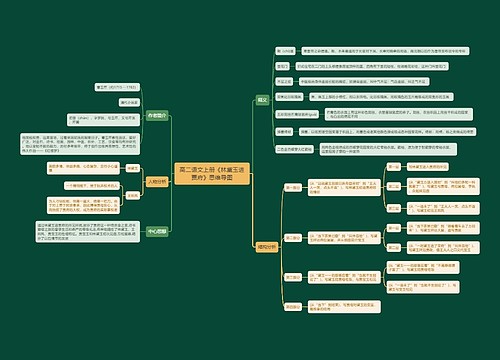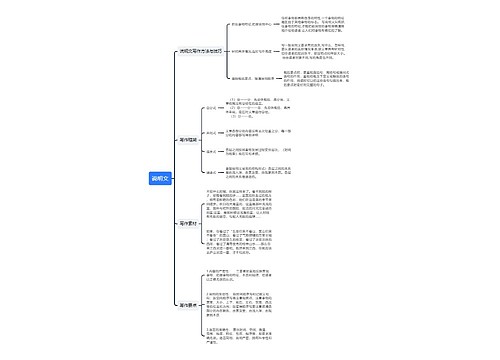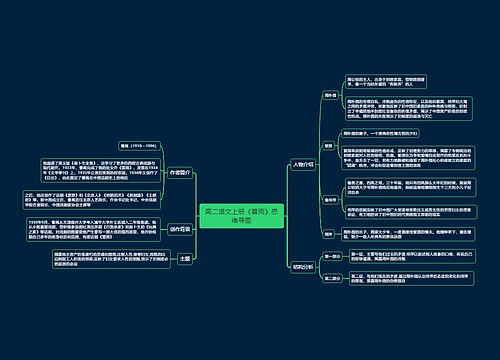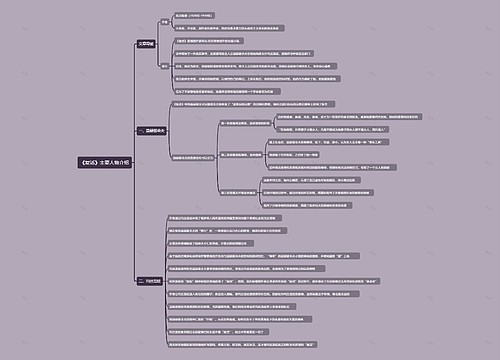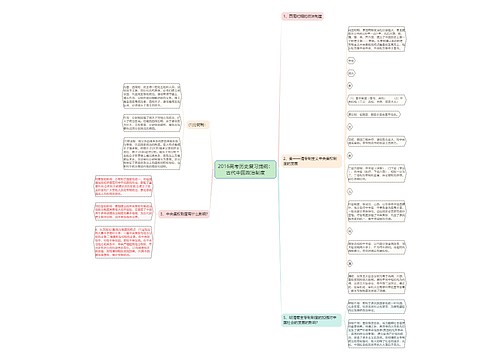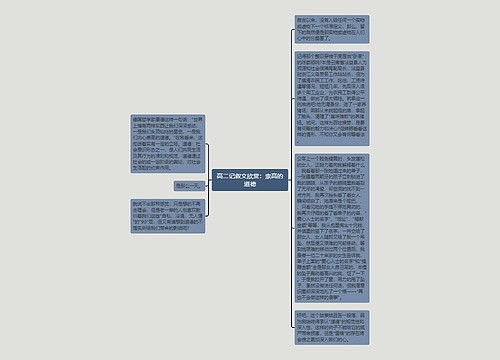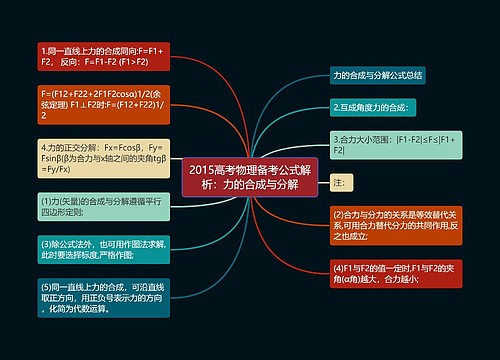高二叙事作文:他的十年思维导图
西风不相识
2023-0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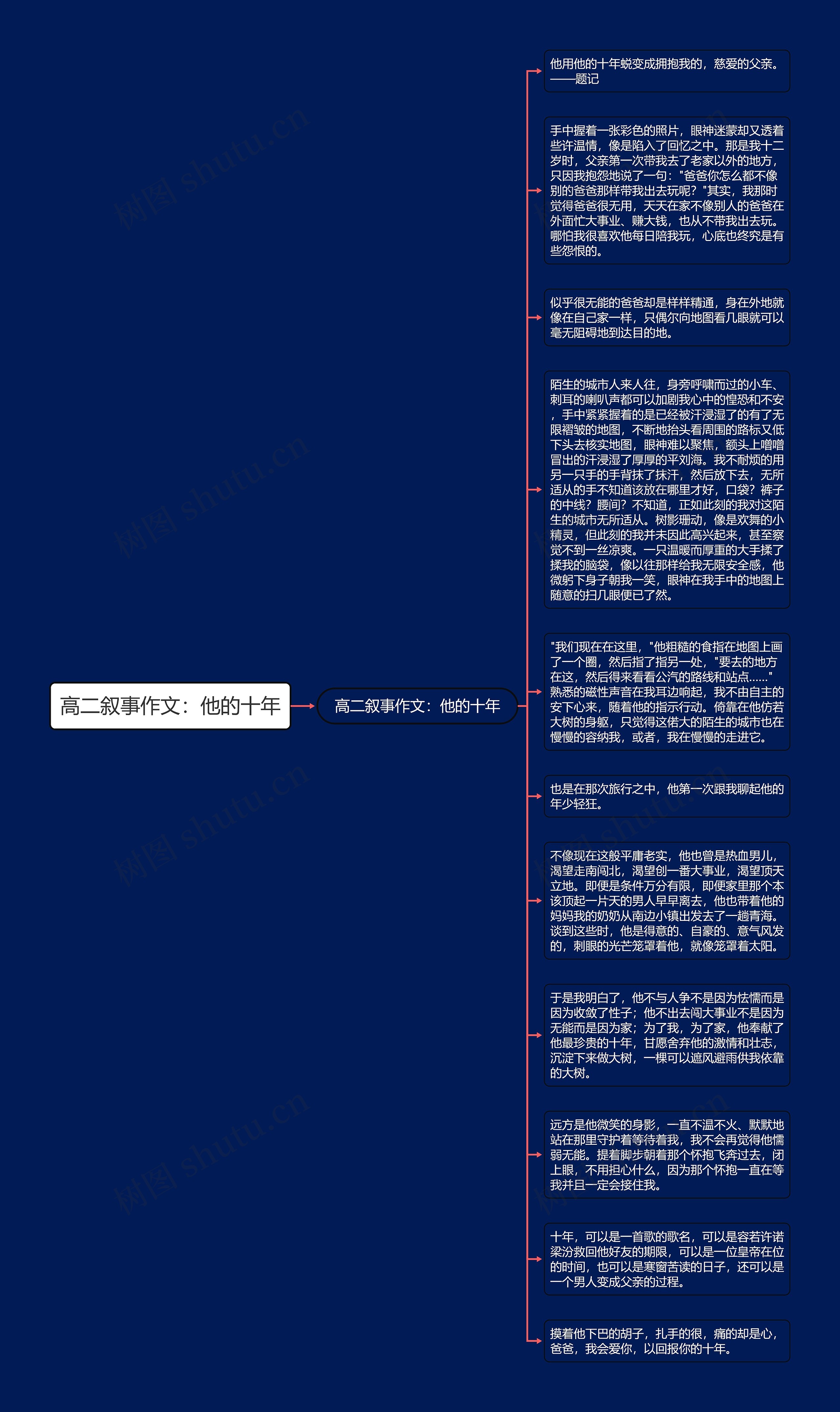
作文是对高中生语文学习的综合训练,主要通过文字来表达一个主题意义。而提高作文写作水平的方法之一,就是大量练习写作作文。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高二叙事作文:他的十年》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高二叙事作文:他的十年》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9290233092fd0bb5cf4b28849b8cb2bf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思维导图
 U633687664
U633687664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10b9a8a2dd2fb4593f8130ef16c320fc

9.战斗的基督教思维导图
 U582679646
U582679646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战斗的基督教》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战斗的基督教》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33d168acd0cd9f767f809c7a5df86e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