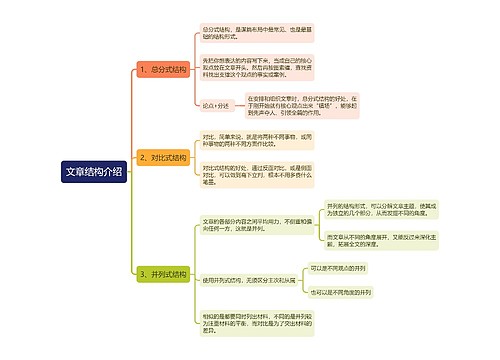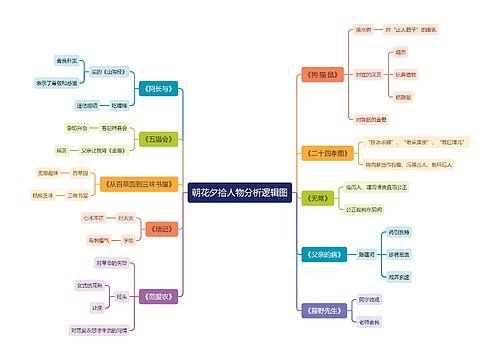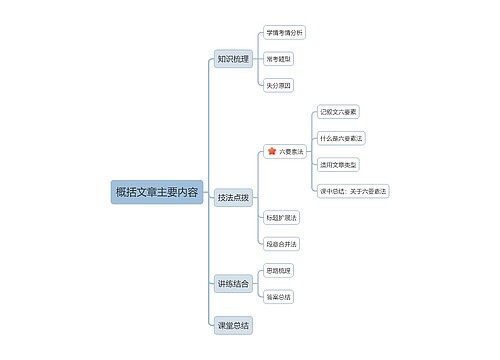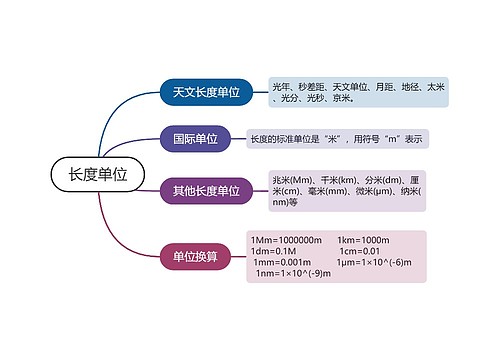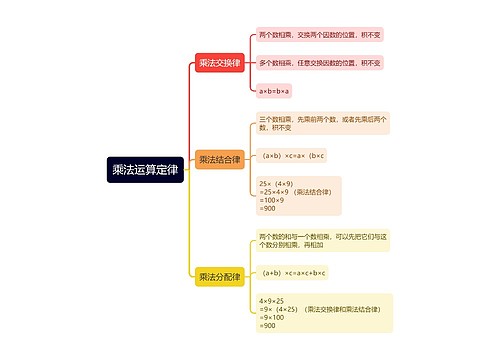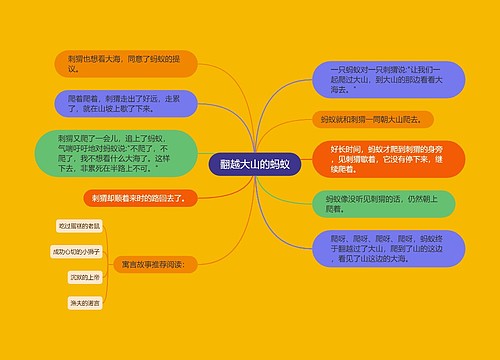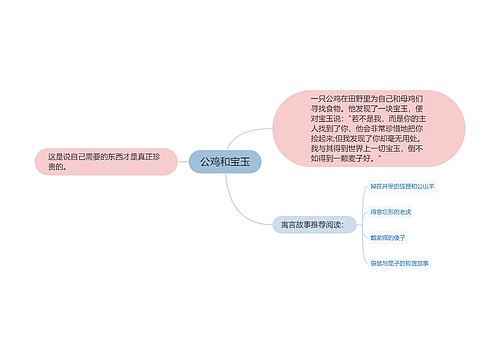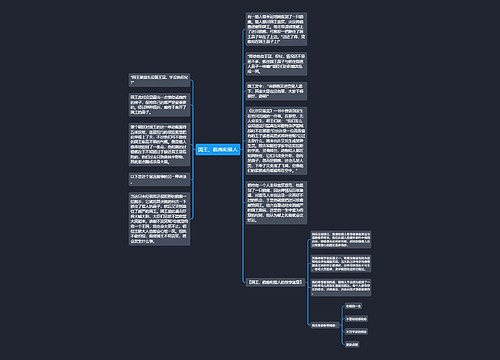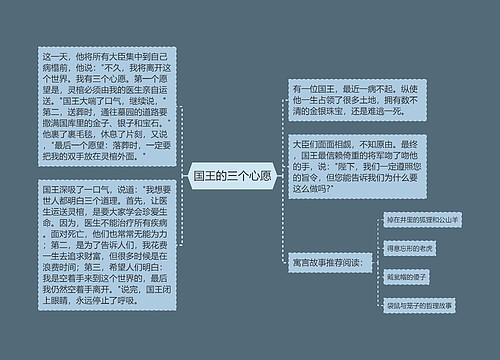当生产队的喇叭嗞嗞啦啦地在村子上空炸响的时候,爷爷转身出了门。出门前,他吧嗒着烟枪,意味深长地说:"家里要添新口了。"不多时,爷爷用一筐青草请回了一头骡子,"啊吁……"一声停在了家门口。谐音的"阿鱼",就成了这头骡子的名字。
阿鱼进门没多久,我们就发现它很怪僻。这只体格强健的马骡,是干活的好把式,拉车、犁地比牛还强,背上能驮五百多斤粮草,就是不让人骑。
哥哥用青草当诱饵,和阿鱼混了几个月,阿鱼才没将喷嚏喷到他脸上。性急的哥哥爬上了它的背,阿鱼触电般地左突右撞,温驯的骡子一下子就变成了狂躁的斗牛。哥哥几下子就被撂了下来,摔得全身散了架似的,再没有骑阿鱼的心思。
不让哥哥骑的阿鱼,更不让其他人骑,它的背上摔下过好多人。驯马师毛蛋对阿鱼不屑一顾,逞强要驯服阿鱼。他的屁股刚挨着骡背,阿鱼就疯了似地颠簸。毛蛋却也从容,拎着缰绳,随着阿鱼的节奏调节身体。阿鱼慢慢垂下头定了下来,大口喘息。毛蛋开始得意洋洋地吹嘘:"别说一只小骡子,就是汗血宝马,俺也……"这时,阿鱼猛地一撅,后腿腾空,屁股朝天,毛蛋被掀到地上。阿鱼又一蹶子,把毛蛋踢得翻了两个跟头。
阿鱼给了所有"霸王硬上弓者"深刻的教训,也在村里打响了"金背"的名头。从此,再没人敢骑阿鱼。
村里有许多关于阿鱼为什么不让人骑的传闻。有人说阿鱼的"爹"是一匹老林里最剽悍的野马。也有人说阿鱼是一匹宝马的种,沿袭了宝马认主的习性。不一而足。
哥哥和我却不管它是什么种,只知道小伙伴们骑着自家的驴或骡在外疯耍,而阿鱼吃了草只会尥蹶子,我们就气得叫它"杂种"!
这反而遭到哥哥对阿鱼更大的记恨。哥哥就往草料中加了辣子面,呛得阿鱼甩着脑袋在原地打转,鼻涕眼泪直流。哥哥看着阿鱼的狼狈样,拍手哈哈大笑,没料想被爷爷几记耳光打得眼冒金星。
爷爷恨恨地说:"不长记性的家伙,阿鱼也是一条生命!对牲口就这德行,将来你对人能好到哪去?"
阿鱼不让人骑,干活却是憋足力气的。所以,爷爷待阿鱼很好,每天半夜起身给它加草料,隔三差五地用自己做的大毛刷给它梳理毛发,农闲时会打来井水给阿鱼冲洗身子,有时竟撇开我们,摩挲着阿鱼的背,自言自语。村里人就说,你家阿鱼金贵得很哪,你爷养了三个娃呦!我们气鼓鼓的,很长一段时间,这都是我们心里的一个疙瘩。
那天,爷爷牵着阿鱼到镇里卖粮,一路毛毛细雨,走到山路时,却突降大雨。阿鱼的蹄子在泥里一拔一拔地,步子越来越沉。
爷爷望着泥泞的陡坡,拍拍阿鱼的头说:"阿鱼啊,咱庄稼人不容易啊,一年到头也拨拉不出多少粮。你再加把劲吧……"
阿鱼好像听懂了爷爷的话,把浑身的皮毛猛地一抖,抖落了一地水,脚底生风似地大步走起来。
回来路上,被雨水淋透的爷爷哮喘病犯了,呼哧呼哧喘得像拉风箱。爷爷捂着胸口咳嗽,踉踉跄跄地栽倒在地。
爷爷强撑着站起来,阿鱼这时却停下了步子,爷爷挥着鞭子使劲地抽打它,它也不走。阿鱼在爷爷的身上蹭了蹭脑袋,把脖子伸给了爷爷。爷爷左摇右晃地就倒在了阿鱼身上。
阿鱼没有像往常一样尥蹶子,而是晃晃荡荡地走了起来,一直把爷爷驮到了一个牧民的家里。
爷爷说起雨中骑阿鱼的事,眼睛里总是闪着光,把一杆老烟枪吸得吧嗒吧嗒响。我们馋得流哈喇子,却嚷着不信。因为,从那之后,阿鱼再没让人骑过。
爷爷待阿鱼更好了,还将它作为教育我们的范本,说:"你们哥俩只有我一个亲人,今后要守本分,要学阿鱼不让人骑,别受人欺啊……"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